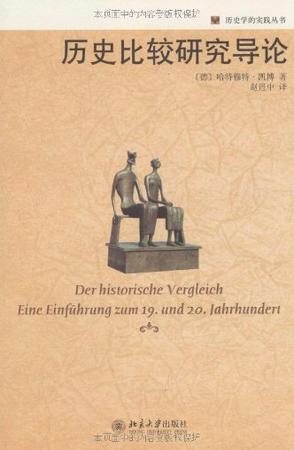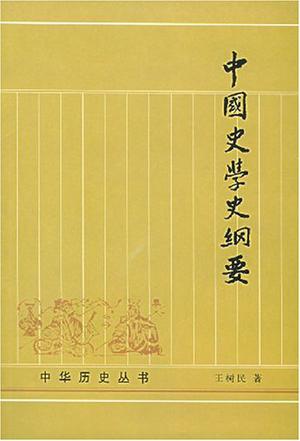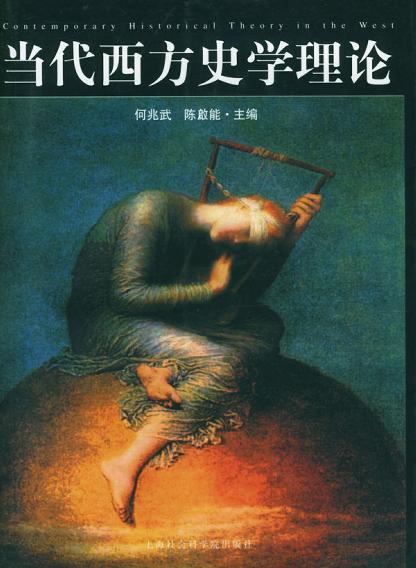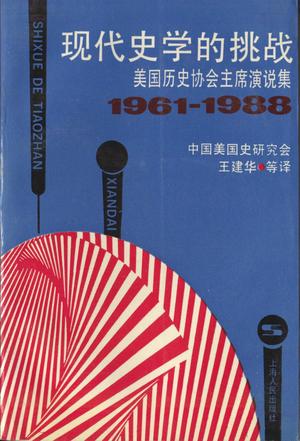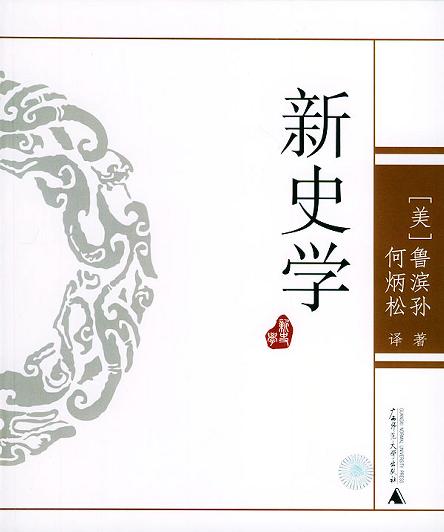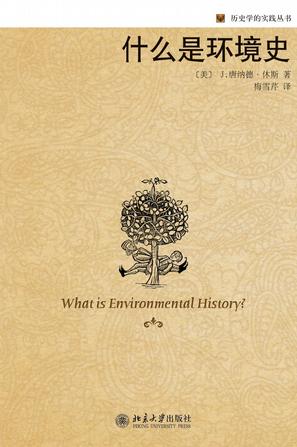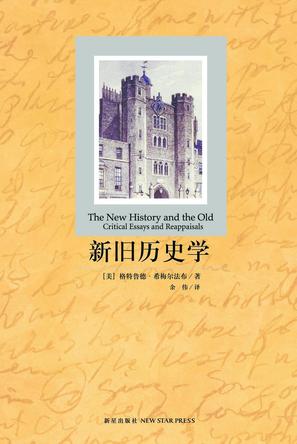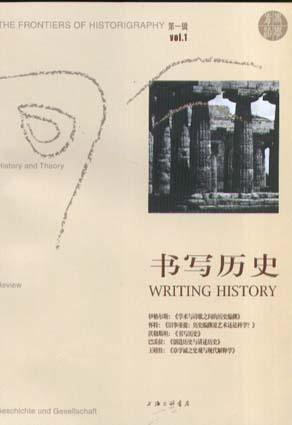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史学理论
-
理论、方法、发展趋势
本书收集了著者近年发表的论文十数篇,从“理论”、“方法”和“发展趋势”三方面,对国际学界热烈讨论中的若干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主要涉及:对“资本主义萌芽”、“早期工业化”、“过密型增长”理论的分析;对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和对海外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评述;以及对该领域新趋势、新视角的分析和探讨。 -
新史学(第二辑):布罗代尔的遗产
布罗代尔是孤独者,也是众人膜拜的对象。说其孤独,是因其强调要克服存在于社会科学中的分割,实行一个普遍的大联合,但时至今日,似乎还不够成功;说其风骚,那是因为他太过成功,吸引了太多眼光,让人难以超越,世界各地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冲力。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影响巨大,他的总体史观与长时段观念不仅成为年鉴学派的支柱性理论,而且超越了学科本身,对人文学科诸领域都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布罗代尔爆冷门,美国历史学领袖之一——早期近代欧洲史专家加莱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觉得挺高兴,但也并非全无微词。虽然他承认该书是“巨大的”、“厚重的”、“感人的”以及“深刻刺激性的”,但仍认为该书在概念和技巧之间并不平衡。马丁利对布罗代尔对“传统史学”的描述以及布氏对“新(‘势不可挡的法国的’史学”的赞美略微有点恼怒,他发现第三部分(最明显地接近传统的,但对他而言也许仍是最重要的)乃是“令人失望的”和“马马虎虎的”。此外,布罗代尔让法国人直面他首选的地域,该意向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布罗代尔通过夸张那被推断描绘和强制延伸出来的“潮湿的撒哈拉荒野”,“轻视了”这个“大海本身”。作为费弗尔的门徒,布罗代尔对航运和航海都有更好的理解,他本来人被迫“修正(他的)许多结论”(Mattingly,1950:351—359)。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们对布罗代尔的杰作回应极少。和他的同事贝林一样,哈佛大学的知识史专家斯图尔特·休斯(H.Stuart Hughes)重申了这种否定。他认为该书不值得列入布洛赫—费弗尔计划(Bloch-Febvre project),断然拒绝接受它;这本书因为“枝蔓横生没有主干”,缺乏“清晰可辨的核心线索”,是难以理解的,并且对欧洲史研究没有重大的影响(Hughes,1968:58)。…… -
历史比较研究导论
《历史比较研究导论》是一部有关历史比较研究之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精炼的慨述。作者哈特穆特·凯博是德国社会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尤为擅长历史比较研究,在本朽中,他结合欧美学界19、20世纪历史比较研究的大量实例,回答了什么是历史比较、如何进行历史比较以及以往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跨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当下,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历史学者越来越重视的一种方法。 -
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
在历经语言学的转变之后,近代知识的“非自明性”问题成为国际历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与此相关联,围绕近代知识的建构而展开的概念史研究、文本比较研究,可谓最受注目的研究领域之一。《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呼应历史学的这一新趋向,以概念?文本研究为中心,收录了以下四组论文: 第一组题为“概念的空间”,收录的论文分别考察了“东洋”、“亚洲”、“自由”概念的生成和语义转变问题;第二组题为“文本政治学”,收录的论文分别涉及《共产党宣言》、《独立宣言》的汉译和文本流传问题,以及汉文佛典《大乘起信论》的英译问题,而明清修志局内围绕如何编纂地方志的分歧,则提供了观察问题的另一个视角;第三组题为“历史学的田野”,承接第一卷的主旨,收录了诠释“残山剩水”之喻与清初士人的“出处”选择的论文;第四组题为“方法的尺度”,收录中外学者讨论中国历史叙述问题的理论文章。 -
今日,何謂歷史?
注定會成為今日歷史系學生的必讀參考書。──亨特(Tristram Hunt) 《今日,何謂歷史?》這書名帶有一個重要卻少人注意到的弦外之音。本書各撰文者會樂於參與本書的寫作,多少是因為它的書名多了「今日」兩個字,讓整個問題變得截然不同。這兩個字暗示著,只要在一轉瞬之間,歷史這學科的內容也許就會變得截然不同。換言之,「今日,何謂歷史?」這問題承認歷史學的本質是流動的。 本書各章探討了許多歷史研究部門今貌,涵蓋甚廣但並未網羅窮盡。它們原是學術會議論文。目的是慶祝卡爾(E. H. Carr)經久不衰而孕育力強的名著《何謂歷史?》(What is History?)出版四十週年。 很多歷史發展都會在本書各章被提到和加以分析。今天,即使是社會史最積極的擁護者,也不會再像六O和七O年代時候那樣信心滿滿,認定社會史無所不包。代之以,他們沈潛了下來,接受了一個更穩健、更現實和更有用的日程表︰不再追求研究社會整體的歷史,轉而視之為研究社會不同方面的歷史,透過擴大研究範圍和吸納鄰近學門新近的許多變化。 在今天許多人看來,近二十年最重要的發展,卻是婦女史與性別史的崛起︰它們因為認識到性別不只是歷史理解與分析的有用範疇,還是必要範疇,遂使得世界一半人口的生活和經驗得以被重新開啟。 今天,許多最頂尖的歷史學家都主張,從解釋走向理解、從原因走向意義,讓我們對歷史的理解變得細緻多了。無疑,不同歷史學門的大批好作品都足以為此說提供佐證。然而,它大概又不是全對的,因為正如卡爾一再強調,歷史學家既推動了歷史過程,又受其束縛。每一代歷史學家都自稱找到打開歷史祕密的新鑰匙——我們這一代亦不例外,而下場說不定也是一樣。這是因為,我們的主張還沒有經歷過時間的考驗。二十年之後,說不定歷史學家的關心會變得非常不同,而且會莞爾於我們這一代怎麼會自信滿滿,深信揭示歷史的「意義」乃是歷史研究的核心任務。 -
中国史学史纲要
历史是人类过去活动的客观事实,简称史实。史实虽是客观存在的,而一时间有密切的联系,时间不停留,转瞬即过,所以历史的最大特点是一往而不复返,不能再现。因而史实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来保持,是为史料。研究历史必须考察史实,而考察史实必须依据史料。史料一般的只能反映史实的某些部分或某些现象,而不能反映史实的全部情况,尤其是实质的部分,所以史料与史实不能划等号。史料的形式有多种,主要的是文字记载,此外有古人遗留的实物,图画雕像,以及口耳相传的传说等。整理这些资料,可以视为史学研究的初步工作,通过可靠的史料,对于史实作科学的考察分析,宣明其发展的规律,方为史学研究主要工作。 “史”字在我国由来已久,“历史”一词是近代从日本传入的。所以我们用“史学史”一词,而不称“历史学史”,不仅因其简明,更因其符合我国的本义。 本书是中华历史丛书中的一册,主要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特点、分期进行了探讨,并详细论述了中国不同时期史学的修订及主要史书的内容,对于概略了解中国史学发展的纲要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
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
思辨的历史哲学无论中外都是古已有之的,而批判的历史哲学却要从19世纪的下半叶开始算起,更确切地说是从布莱德雷1874年《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一书的问世算起。本书是布莱德雷在1874年发表的最重要的一部哲学著作。尽管篇幅不长,但它却是批判历史学的哲学反思的标志性的开山之作。同时,本书适合作为布莱德雷哲学的入门读物,其中不仅蕴含了其思想的若干要义,而且体现了他鲜明的哲学风格,例如典型的轻视例证,以及按照现代标准来看艰涩的行文。 -
史家的誕生
在中文世界,誰是當今首屈一指的史學名家?海峽兩岸共同浮現的人名,很可能又是「陳寅恪」這個人名。但陳氏去世很久,還活著的史家中有誰可以戴上中文世界一代名史家的冠冕呢?不同的從業人員可能各有心目中的人選。無論如何經票選出的前十名,再怎麼說都無法與西方史學先進國的一代大師相提並論。使用中文的史學後進國經八十年的「新史學運動」,依然無法迎頭趕上她當年的西方史學師尊。中國這個現代西方史學的徒弟,耗費了三至四代的努力,一提起代表中國的史學大師,眾口交譽的陳寅恪又是何許人呢?陳老先生生前遭胡適譏諷他的作品在表達上是不及格的。胡適所言倘若公允,則近百年的中國史學大師其特色竟是文字表達不及格的一個人。這樣的史學大師在西方看來會是個胡鬧的笑話,可是在中、台兩地則是個神話。陳寅恪已經是被神格化甚久的一位史家。 同樣問題問西方世界,則少說有三、四十人之多是他們的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的造詣比起這些洋同行不僅相形遜色,而且他那一筆文字表達也太令人不敢恭維的了。有一天,陳建守在跟我談翻譯西方史學大師訪問文稿的計劃時,我總覺此事難的是如何從三、四十位名家中精挑出十位、然後再編輯一本書。在這裡,你會有抉擇的痛苦時光。建守在考上研究所後因病休學,只能窩在鄉下養病。可他又不想沒事做,他就去做擬出西方史學大師十人名單的事。接著他不憚其煩地去與他心儀的大師通信,一年下來竟然成績斐然。這十位大師不僅告以刊登何篇訪問或側寫為其最愛,抑且倘若無有滿意者,則親力為之,這在全書有一篇。這是本編輯的一大賣點。此外,這些大師還儘可能授以翻譯的版權。建守病癒返校乃著手邀集好手翻譯這些西文文章。大約一年左右,這些譯稿先後交抵建守手中。再經過一番整編以及其他手續,這本《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總算大功告成,只剩付梓一途。這書在印製之前,建守囑我寫篇「導讀」以資紀念。我想此事既由我起頭,如今又收功在即,講些對讀者有所助益的話,應該不是什麼多此一舉。 上一世紀西方學術界展開兩波新史學運動,第一波發生於六○、七○年代,此即我們熟知的社會史課題正當性的確立。這波運動約有二十年榮景。就在社會史研究取向的一片榮景聲中,另一波改革議程悄然啟動,時為七○年代,也就是今天兀自沛然莫之能禦的新文化史運動,迄今抑且不知伊於胡底。每個時代都有代表其特色的學風,每種學風下的傑出之士就是一時之選的人物。二戰後的西方史界,其學術氣候之變就在於從社會史轉變成新文化史。 編者所選的十位明星大師,美國史家計有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Z. Davis)、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多明尼克.拉卡頗(Dominick LaCapra)、羅伯.達頓(Robert Darnton)、以及林.亨特(Lynn Hunt)等五位,法國史家計有達涅勒.侯胥(Daniel Roche)、阿蘭.柯班(Alain Corbin),以及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等三人,英國和意大利則各以彼得.柏克(Peter Burke)和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分別代表。這些人的聲名對台灣史研所研究生而言早已如雷灌耳,他們作品中已有多本中譯、且流通兩岸之間。這次十位大師在同一舞台一起現身和亮相,等如讓台灣史學初習者近距離親炙大師一般。 十位中有五位的家世背景欠佳,像戴維斯女士和金茲伯格先生都是猶太人,柏克先生的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則有波蘭和立陶宛的血統,亨特女士為德裔第三代,懷特先生的父親是工人。少數族裔和下層社會的出身對上述五位史家並未構成上進的障礙,相反地,還有助於構思多元文化價值,更對他們從事庶民文化研究時平添異想不到的秘密武器。其他五位中,達頓先生應該來自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其餘四位家世不明,但很可能出身文化菁英家庭。庶民文化對這五位而言是異文化,卻不僅不排拒,還設法思所認識,更是彌足珍貴。 這一波新史學運動其學術靈感得自法國年鑑史學所標榜的「心態」(mentality)的研究課題。七位非法國史家中有五位與法國史學有著程度不一的關聯,由深至淺而言,達頓長期與年鑑史學團體有合作計劃,亨特到過法國留學,柏克則私淑布勞岱的「全體史」研究境界,戴維斯則長年在法國蹲點作研究,以及拉卡頗因研究法國文學文本而與法國學界有所關涉。這些例子正是英美史界與法國年鑑史學互動的絕佳例證,年鑑史學作為西方當代史學重鎮正可從此一側面窺知一、二。 新文化史家在對歷史的認識上不失歷史相對主義的軌轍,但這十位之中,唯獨金茲伯格一人非常反對歷史相對主義的提法,仍然對真相的提法情有獨鍾。他認為在論證過程依傍證據一步一步推求事理,離真相應該是雖不中亦不遠矣。這十位史家對歷史相對主義的堅持程度上高低有別。倘若系譜的右端代表的是歷史相對主義較低的界域,則此界域的掌旗官非金茲伯格莫屬,然後依靠近他的順序會是達頓、夏提葉、侯胥、柯班,以及亨特等五人;系譜的左端其中流砥柱則會是懷特,至於柏克、戴維斯,以及拉卡頗等三位,則依序靠近懷特。系譜右端的史家集中興趣在身體感知系統和內在精神狀態;系譜左端的史家則比較偏好看待事物的表述(representation)方式。也就是說,一邊關心的是人類體驗的經驗,另一邊則關懷人類認知事物的方式。但無論如何,都不是舊日史家措意的所在。 體驗也好,認知方式也罷,菁英能,庶民何嘗不能?這次新文化史家刻意經營的卻是庶民文化。柯班之於法國食人村的村民,柏克之於歐洲近代大眾,戴維斯之於里昂下層社會的一眾男女殺人凶手,亨特之於大革命時期的革命追隨者,侯胥之於巴黎日常生活場景的庶民,達頓和夏提葉之於平民大眾的閱讀行為,拉卡頗之於劫後餘生者以及關心受害的平民大眾,金茲伯格之於十六、十七世紀與教廷格格不入的農業文化傳遞者,這些都是我們賴以辨認這些史家的招牌商標。這之中有一位倒是例外,那就是懷特。他對於史家書寫歷史、表達歷史的方式一往情深,指出了文學與歷史的親緣性這一點,劃破了歷史與文學是在求真和虛構的邊界。 講到文學,這些史家都文采曄曄,很長於寫作,而且其中不乏多產者。像柯班於1973年博士到手後的十餘年時光就出版十本專書,柏克也有十本專著,他可以右手著史,左手寫學術社群的書寫文化。金茲伯格不論在《夜間的戰鬥》,還是在《乳酪與蟲子》中,整體書寫如行雲流水,活脫是說部。達頓先當過新聞記者,寫起歷史來頗有報導文學的架勢。戴維斯的成名作:《馬丁蓋赫返鄉記》,就是一本故事性十足的史書,還被好萊塢據以改編拍成電影。她的《檔案中的虛構》透過一則則司法案件串連而成,展現的正是非凡的講故事功力。這是一本高難度操作的史書,難得的是饒富閱讀趣味。柏克的文字明白曉暢,講起事理來開門見山,不事蕪雜,無怪乎他的中譯本有十一本之多,幾乎在中文世界可以推出全集了。其餘史家其文風各具特色,就無庸贅述。要之,新文化史家的作品除了故事張力十足之外,文字工夫更是深有講究。這一點是中文世界的史家所無法與彼輩比肩的地方。還不值得我們同行痛下決心、徐圖改進嗎?觀他人、想自己,能不聳然以懼嗎? 十九世紀西方,歷史學相較於其他新成立的社會科學,顯得弱不禁風,為了取得學科認證的正當性付出了相當的努力,以迄於今尚能屹立不撓,歷代史家的業績是有目共睹的。在此,有一點是值得重視的。歷史家在與其他社會科學學者的對話方面,理論的講求還是不能掉以輕心的事。歷史知識與社會科學知識之間能否交流,很大程度上端在理論取向是否被史家懸為冶史的圭臬。歷史家對於理論的講求不是在為既有特定理論背書,而是理論性的自覺,俾便加強作品的深度。學科分立有分立的好處,但有許多重大問題是處在既有學科的三不管地帶,除非史家不想作重大問題,否則學科分立只會徒然造成畫地自限的反效果。柏克在處理路易十四公共形象的模塑上,如果不借助媒體研究,該書的可觀性勢必大打折扣。同樣,戴維斯在鑽研赦罪書文本時,沒文學批評關於敘事的素養,我不信她會想到說故事的文化。還有,亨特不去修習心理學的話,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現象恐怕也不易發現吧?這些例證都告訴我們史家不能以學科界限為滿足,要進行跨學科的探究,才能發現前賢未及之處。堅守學科本位的姿態往往是掩飾自己不思進取的藉口罷了。跨學科的思維不見得是治史學的絕佳利器,但堅持學科本位有讓中文歷史學更加茁壯嗎? 這些新文化史家的作品還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創意十足,而且不使招式用老。柏克處理過的課題計有,文藝復興的文化菁英、西方近代大眾文化、領袖的公共形象營造、西方知識霸權的崛起,以及不同媒介設施的知識傳播等。戴維斯處理過冒名頂替的司法審判、說故事文化的變遷,以及女性的主體意識等課題。柯班處理過地方史、物化女性、嗅覺感官文化的塑造、視覺感官下海岸的發現、聽覺與政治的關係,恐怖心理的投射等課題。他們都擁有好幾把刷子,往往不讓前一把刷子的招式用老就換另一把刷子。每一部史著都是一個新天地,這是一種狐狸型的學術性格,正是國內史學界的絕大多數史家所欠缺的治史方式。這些新文化史家不僅花樣百出,而且層出不窮。他們讓文化概念呈現一種複數形式,每一本史著就是一種具體而微的文化概念操演。不像國內史家將文化界定為單數而且是唯一的一個,動輒不是講「中國文化史」,就是誇稱「台灣文化史」,活像古往今來只有一種,而且只有一套國族屬性的文化。這是文化思維的改變,是國內史家從未想過的一種新治史經驗。 將文化界定基於複雜思維,固然舉出林林總總的文化面向,但也因此不免流於瑣碎之譏。這些名家中不乏有人對瑣碎治史引此為誡。如果西方史家發掘出各式各樣的文化之餘,良莠不齊的結果,那些莠草般的作品就教人不敢恭維的話,那麼,國內一向崇尚瑣碎為治史不二法門,豈非一開始就走向莠草化的史學之途??的確! 國內史界長期欠缺閎觀、鉅視的心眼,做的歷史往往見樹不見林,卻以此自視高人一等,用以譏嘲一般非其同行不懂他及其追隨者採用被研究時代人物的用語。他們以堅持用古代用語為得計,而不知歷史書寫的讀者群是現代人,既然如此,就有義務要將古代用語譯成今語。像唐代的「犯?」罪,就一定堅持不用貪污罪。彷彿借用今語的貪污罪會減損其唐史專家似的。像這樣的唐代法制史研究,寫再瑣碎不堪的小文章也不足以解決任何歷史重大問題。一位史家如果不能使用現代語言來說明、或詮釋古代歷史現象,他還算活在現代的人嗎?唐史研究不是作給唐人看的,而是要作給現代人讀的。如果這種標榜唯瑣碎是尚的學風不消除的話,莫說同是治唐史的人只因不研究法制史以致看不懂專家之文,遑論一般讀者了。無怪乎這種唐代法制史專家一輩子寫不出一本專書了。用瑣碎思維想問題,只能將歷史枝節化,窮其一輩子只能見樹卻不見林!我們社會一點都不需要這種史家,偏偏這種史家拿了一堆國家冠冕,諸如傑出學者、院士,以及講座教授等等不一而足。台灣的學術桂冠也未免太過於廉價了! 上一世紀二0年代中國新史學運動以來,在以西方新史學為師,卻學得四不像,處理的問題過於瑣碎化是其病癥之一;病癥之二即是不知運用現代語言作為溝通古今的媒介;病癥之三不知使用敘述史學的方式來重建歷史,導致史學為廣大社會所揚棄。這三蔽是我平日觀察心得,並非這十位史家深曉中文史書之蔽。抑有進者,三蔽中,除了第一蔽是西方名史家引以為誡的一點之外,其他兩蔽在西方是不會有的事,理由是史家是為今人著書立說,焉有自絕於讀者之理?這十位史家萬萬不會想到今天中文主流史家會自絕於讀者至此境地。這本書有引介未來西方史學萬神殿中十位神祇之功,大有照見中文世界史學三弊的勸世良方之況味,值得下一輪的史學工作者嚴肅看待臺灣出版本書的不尋常意義。 八十年來的中國新史學運動,並未使中文史著躋身世界名作之林。一些受封、或自封的史學大師其實仍是井底之蛙,他們拒絕成長,對於有益他們成長的外部刺激向來是嗤之以鼻。史學的年輕世代如果要以當井底之蛙為己足,那就不必理會本書所提供的外部刺激吧。在攀越西方史學的高?絕壁之餘,在回視中文世界史學的落伍和保守,就像參訪一座城市由高級住宅區迅速變成貧民窟的滑落感。 本書精挑細選十位當代西方史學名家的介紹文稿,他們分別是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海登.懷特(Hayden White)、達涅勒.侯胥(Daniel Roche)、阿蘭.柯班(Alain Corbin)、彼得.柏克(Peter Burke)、羅伯.達頓(Robert Darnton)、卡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多明尼克.拉卡頓(Dominick LaCapra)、侯瑞.夏提葉(Roger Chartier)和林.亨特(Lynn Hunt)等人。透過編輯的訪問或側寫,讀者可進而獲窺當代西方史學的百官之富,並藉此與西方史壇順利接軌。抑有進者,本書還選譯針對「新文化史」研究進行反思的文稿,該文是首次以翻譯形式在原產地境外的國家發表,這是本編的一大特點。這本《史家的誕生:探訪西方史學殿堂的十扇窗》等於是讓這十位大師在同一舞臺現身亮相,如同近距離領略大師風采一般,讀者可千萬別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评价西方史学理论一百年来发展史的专著。 本书内容不仅包括历史哲学方面的重要流派和主要代表人物,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史观、自由主义、生命派的历史理论、分析的历史哲学等,还包括当代西方重要的史学流派的理论,如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美国新科学史派等。此外还有当代自然科学与史学、苏联及中国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 本书的特点尚有: 一、各章都由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执笔; 二、各章作者都是根据原著和第一手资料写成; 三、各章夹叙夹议,注意分析,是一部研究性的作品; 四、注释详尽,资料翔实,文字深入浅出; 五、作者注意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对西方各个流派和代表人物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 -
历史主义
在这部小书中,作者以其对欧洲的历史思想与实践的广博学识,简要阐述了“历史主义”的内涵及其在欧洲各大民族历史传统中的差异。作者在论述历史主义的现代特征及其对欧洲思想的贡献时,也分析了历史主义与近代欧洲历史命运和政治思潮之间的关系。 -
元史学
简介: 本书系海登·怀特的成名作,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作者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理论,同时又注重贯彻历史主义思想,并以反讽式的比喻策略对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逐一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进行历史著述时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导读: 《元史学》肯定激起历史编纂学的论争,并成为这个领域中的经典。……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历史学家都不应忽视这本书。 ——《历史》 ……富有雄心和挑战性,试图说明所有历史思想,无论出自实际写史的人还是历史哲学家,都依赖于“历史想像的深层结构”。 ——《太平洋历史评论》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 译者的话 1966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历史与理论》上发表了《历史的重负》一文,从此,他步入了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前沿领域。1973年,怀特的著作《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以下简称《元史学》)出版,它不仅成为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也代表了20世纪下半叶历史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如今,我们以过去三十年来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状况为参照,审视怀特在《元史学》中呈示的研究目的、思路、结论与逻辑,应当对我们把握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脉络有所助益。 一、诗性预构先于理性阐释 怀特在《元史学》开篇引用了巴什拉的箴言:人所能知者,必先已入梦。常识中,梦想若以文字表现出来,必不容于以求真为目的的史学领域,因为梦想是诗性的,不能“理”喻。然而,怀特相信,史与诗并不存在截然断开的鸿沟,任何史学作品都“包含了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学的,实质上,特别是语言学的,并且充当了一种未经批判便被接受的范式”。于是,《元史学》便准备担负起一种使命:旨在确立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当然,论证这一根本目的的同时,怀特也将藉此展示“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 。这便是他在研究前预期赋予《元史学》的两项理论成果。 如果把写作《元史学》视为怀特的“历史的”实践,那么,我们一开始就必须记住,这两项理论成果首先是怀特在实践之前的假设,也就是说,《元史学》是对这些假设所做的证明,而并不是要发现某种永恒、确定的历史本质。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种姿态或者说解释策略与传统历史学家的方法有极大的区别,正是如此,我将表明,《元史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它本身的写作实践上都是反传统的先锋。 早在1966年,怀特对历史学传统的不满已经清晰地表现在《历史的重负》一文中。他反对的传统是那种造成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的学术语境,它的实际结论事实上是确认历史学处于艺术和科学这两种认知方式的中间地带。怀特不满意历史学家在遭遇社会科学家的质疑时声称自己要依赖直觉因而是艺术;在面对艺术家的批评时则声称历史资料不容辩驳因而是科学。自19世纪以来到20世纪中叶,历史学家的这种费边式谨慎策略虽然使自身可能逃避单方面的批评,但怀特认为,如此模棱两可恰恰是当代历史学陷入了重重危机的根本原因。怀特主张,历史学应该像科学和艺术那样更新观念,而不应束缚于现今仍坚持的19世纪末的科学观念和19世纪中的艺术观念中。他注意到“迄今为止近三十年来,科学哲学家和美学家都致力于更好地理解科学陈述与艺术陈述两方面的类似性”,科学与艺术都“发现它们用来理解一个能动的世界的那种隐喻性构造本质上具有临时性特征”。历史学只有大胆地利用当代科学哲学与美学的最新成果,才可能重新确立历史研究的尊严。 我们可以将《历史的重负》一文视作怀特批判传统历史学的宣言书,它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理论思路。该文充分注意到当时科学哲学与美学在认识世界时的 “建构性”和“临时性”(“时间性”)策略,注意到历史学和隐喻之间的密切关系。应当说,《元史学》中的理论胚胎已经在这篇论文中初具雏形。怀特沿着这条思路,到70年代初写作《元史学》时,他在诗性想象和比喻理论方面的思考要精深得多,并且,《元史学》的丰富例证同时又代表着作者为表述一种新的理论框架而进行的史学实践,意在阐明19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的发展如何导致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历史主义”危机。 建构、想象和比喻,这些曾经都是传统历史学家排斥的东西,却被怀特用来充当其史学理论大厦的基石。怀特认为历史叙事是建构而来,它之所以为建构的产物是因为史学家“通过建构一种理论的推理论证,来阐述故事中的事件” ;另外,这种理论的推理论证又靠一种历史学的语言规则来实现,它又是诗性建构的结果。在怀特看来,这些建构归根到底是发生在理性阐释之前,因而也是一种预构。既然预构行为普遍具有“前认知的”和“未经批判的”特性,它自然要隶属诗性的范畴。怀特接受了维柯关于诗性智慧的思想。我们记得维柯曾宣称:“诗人们首先凭凡俗智慧感觉到的有多少,后来哲学家们凭玄奥智慧来理解的也就有多少。”如果将诗人的感官与哲学家的理智都结合在怀特的理论中,那么,诗性的预构行为便决定了稍后要进行的理性阐释的深度与广度。怀特确实是遵循这样的理念,他要在《元史学》中证明每一位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的诗性预构行为最终都构成了他们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历史哲学。当我们将诗性预构的概念作为怀特理论的一部分而纳入理性的解释系统,这一理论的前提便是相信历史叙事中诗性预构先于理性阐释。怀特以19世纪欧洲八位主要的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的历史写作为例来证明这一点。当然,支持怀特进行证明的理论并不完全是他的独创,它是怀特综合了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语言学、艺术和哲学许多成就的结果,这正是一种怀特在《历史的重负》中推崇的、当代科学与艺术为历史学提供的新视角。 二、形式主义方法与结构主义理论框架 历史著述理论与语言规则是支撑起怀特论证的两大支柱,藉此,他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一套独特的结构主义理论框架。 一开始,怀特将历史著述分成五个层次,它们分别是编年史、故事、情节化(emplotment)模式、形式论证(formal argument)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ideological implication)模式。他把编年史和故事看成历史讲述中的原始要素。与以往不同的是,怀特认为“创造”这一往常和小说创作相关的概念其实在编排历史故事时也起作用。历史学家从编年史中挑出什么样的事件编成故事实际上与他们编排故事时已经预料到的问题有关,换句话说,史学家是为了回答他的问题而选材。再进一步,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便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种种方式。由此可见,明确认识到历史叙事过程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是怀特理论的出发点,这是从年鉴学派历史家们、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以及哲学家伽达默尔等人那里吸取的养分,怀特自觉地运用在他的理论中。 在论述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三种解释模式时,怀特都为它们更细致地区分了四种类型,我们列表如下: 情节化模式 论证模式 意识形态蕴涵模式 浪漫式的 形式论的 无政府主义的 悲剧式的 机械论的 激进主义的 喜剧式的 有机论的 保守主义的 讽刺式的 情境论的 自由主义的 对怀特而言,以上三种模式都有其学术来源。他区分四种情节化模式是借用了诺斯罗普·弗莱在《批评剖析四论》中提示的线索;根据斯蒂芬·佩珀在《世界的构想》中的分析区分了形式论证的四种范式;而细分四种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的思想则借鉴了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分析。 在怀特看来,形成历史故事的事件序列正是通过情节化方式逐渐展现为某种类型的故事,如悲剧、喜剧故事等等。当史学家在选取某种情节原型来表现历史故事时,他就在按照该原型的结构来解释和确定故事的意义。形式论证模式不同于前者,它要用一般因果律来说明引导着一种情形向另一种情形转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即为表述确定时空范围内的要素提供一种言辞模型,它直接牵涉到历史实在的本质,若用类似于佩珀的话说,则关系到我们是按机械论还是按有机论等等范式来构想我们的历史。关于意识形态蕴涵模式,怀特首先确认他所说的“意识形态”是一系列促使我们在当前的社会实践范围内采取某种立场的规定,它决定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现实、看待往事。 以上三种模式在历史叙事中各有侧重点,情节化模式针对的是所发生事件的内容,形式论证模式关注解释的外在形式,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侧重解释中的伦理因素。在讨论这三种模式之间的关系时,怀特指出,代表着历史作品中伦理环节的意识形态蕴涵模式“能将一种审美感知(情节化)与一种认知行为(论证)结合起来” ,从而在描述性(情节化)和分析性(形式论证)陈述中获得一种说明性(意识形态蕴涵式)陈述。三种模式如果按特定方式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史学家独特的编纂风格。这样,仅仅根据上文列表可以算出,历史编纂至少可以有64种风格,只是怀特认为,它们并不能任意组合搭配,历史编纂仍须依循结构上的同质性,它决定了情节化、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之间那些“可选择的亲和关系”(elective affinities)。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一些史学大师并不按部就班,顺应种种“可选择的亲和关系”,他们总是要将某种情节化模式与本不协调的论证模式及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结合在一起,如米什莱结合的是浪漫式情节、形式主义论证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蕴涵,布克哈特结合的是讽刺式情节、情境论的论证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是什么支持着这些史学大师在一种不协调的氛围中创造出在读者看来是一致性和融贯性的历史图景呢?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怀特进入了历史意识的深层结构。他认定,正是在本质上是语言学的诗性基础之上,史学大师们借助于种种概念性解释策略创造出了最终的一致性和融贯性。 怀特揭示的这个创造性过程是这样的。他认为,历史学家在理性阐释历史材料(即在认识论的范畴下进行认知)之前,先需要将历史领域想象成某种精神感知客体,而要想说明这个客体,他又必须将该领域中的现象区分成诸类要素,此时,也就意味着他设定了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诸种关系产生的“问题”则正是接下来的情节化和形式论证作为认知模式要加以阐明的。这就是说,对史学家而言,历史领域是什么、它包含些什么要素、区分诸种要素应根据何种概念,而阐明要素之间存在的问题又要选择怎样的策略等等,这些都是诗性想象的结果。据此,怀特相信:“在先于对历史领域进行正式分析的诗意行为中,史学家既创造了他的分析对象,也预先确定了他将对此进行解释的概念策略的形式。” 怀特理论的下一个环节转向了比喻理论。他在实践自己的另一项任务,即把语言学成果运用到历史哲学之中。我们能够判断,使语言学中的比喻理论与历史叙事理论之类比成为可能的前提有两个:其一,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认识到历史叙事是语言的产物,它必须服从语言学规则;其二,诗性想象与诗性语言具有感觉上的类似性,因而有关诗性语言的理论可以有效地运用在具体化诗性想象的历史叙事之上。怀特在《元史学》中并没有阐明这两个前提,但他在论述中却直接以语言学原则类比历史叙事原则。 鉴于前述三种模式搭配组合而构成解释历史领域的繁杂性,怀特进行了一些简化。他强调,可能的解释策略其实并不多,其中有四种常用的策略对应着诗性语言的四种比喻,它们是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运用这种比喻理论,我们就有能力将某个特定时期内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分类阐述。怀特认为,每一位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对历史领域的想象及其提供的解释策略都是某个话语传统中的一个环节,而这个话语传统的发展乃是“从人们对历史世界的隐喻式理解,经由转喻式或提喻式理解,最后转入一种对一切知识不可还原的相对主义的反讽式理解”。具体以19世纪欧洲主流的史学思想为例,怀特将19世纪历史意识的发展描述为三个阶段:超越反讽阶段;热情研究历史,对历史实在充满信心的阶段;危机阶段或反讽阶段,也是历史解释多元化盛行阶段。不过,在这最后一个阶段,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中都再次出现了超越反讽的努力。史学界从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到布克哈特,历史哲学界从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到克罗齐都演化出这个历程,于是,作为特定时段的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及历史意识的发展就这样在怀特的理论框架中得到了解释。 怀特在《元史学》中使用的是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一种结构主义理论。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我是说,一个形式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的确,我们不难看出,怀特的理论有着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他相信从隐喻、转喻、提喻到反讽构成了一个可以自我调整的闭合循环,这是一个结构上的整体。他以四种语言学规则来类比四种历史意识模式,并通过融入历时性因素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演变,在这个由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构成的历史意识变化结构内,19世纪欧洲史学思想经过反叛18世纪启蒙时代后期的反讽式历史图景,于19世纪末又回归到一种类似的反讽式图景中,这其中既包含一种历史情境的转换,也体现出历史意识的自我调整。在赋予历史意识发展某种结构的同时,怀特用一种形式主义的解释策略来编排19世纪的历史著述,当他声称自己是形式主义者时,他指的是自己的《元史学》是在尝试以形式主义的方法对某个特定的思想史领域(此处是史学思想史)进行了一番梳理,这种尝试以前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实践过,而历史文本是首次成为形式主义方法实践的对象。怀特认为,《元史学》对19世纪史学思想的形式主义解释成功地向读者展示了当时主要的史学思想家“占主导地位的比喻方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即他们写作中不可还原的“元史学”基础,《元史学》之名的立意也在于此。 三、理论表述与叙述实践的张力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怀特《元史学》中的结论:一、任何史学作品都蕴涵着某种历史哲学,它们与传统上史学家们曾排斥的历史哲学作品一样,有着相同类型的解释模式可供选择;二、任何解释模式的存在都意味着它是一种诗性领悟的体现;三、因为形式化的解释模式根本上是诗性的、外在于认识论原则的,它们彼此不可比较、不分优劣,叙述者最终选择哪一种只能依据他自己的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史学的科学化倾向不过是诸多选择之一。 若我们以彼之道施于彼身,用怀特的一般结论为准则来评判、反思《元史学》,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怀特又是如何消除其理论表述与叙述实践之间存在的辩证张力而获得一致的历史图景呢? 为了使自己的理论自圆其说,怀特对上述可能的疑问都有所准备。我们已经知道,《元史学》作为一个整体,其论证模式是形式主义的;在情节化方面,正如怀特在序言中也主动声称,他采取了讽刺式模式;在意识形态蕴涵方面,怀特更像一位激进主义者。这样,按照怀特的理论,讽刺剧、形式主义和激进主义共同构成了怀特史学的风格。在他研究的19世纪史学家和历史哲学中,怀特的风格与马克思的最为接近,以至于他后来坦言,“我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直如此”。与怀特所研究的马克思有所不同的是,他对反讽有一种强烈的自觉性认识,甚至可以说,怀特相信唯有通过这种对反讽的自觉意识,才可能缓解他的理论表述与叙述实践之间的张力。 毫无疑问,《元史学》本身的反讽姿态所针对的正是怀特在《历史的重负》中批判的传统史学及其认识论。这种反讽除了出现在对具体史学发展阶段、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思想的评判中,还更多地表现在怀特陈述他的理论前提时。怀特习惯于用“我假设了……”而不是“我发现……”,例如,怀特声明:“为了将这种不同的风格彼此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史学思想的单一传统的诸要素,我不得不假设一种意识深层”,“在具有赋义作用的预构(比喻性)策略基础之上,我假设了四种主要的历史意识模式,即隐喻、提喻、转喻和反讽”。此处,在怀特的语境下,向读者表明前提和假设具有两层意义:其一,告诉读者,如果读者认为《元史学》的论证分析合理,那么它的合理性将以这些前提假设,而不是以某种客观存在的本质内容为基石;其二,既然整个理论的基石都不过是一种假设,一种预构,那么对于19世纪欧洲史学思想,读者就应该存在提出其他前提假设从而构成另一种理论分析的可能性。怀特自觉表述了其理论前提的假设性质,若在以往一味追求唯一性解释的历史学传统看来,这不啻于自毁长城,但这却是怀特刻意表现的反讽姿态,以亦此亦彼消除了那些坚持非此即彼的人可能激发的质疑。 反讽是怀特采取的一种比喻策略。如果说它代表着一种老于世故和玩世不恭的意识状态的话,怀特却也有他的“正经”目的。他曾经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读者不可能注意不到,本书正是采用了一种反讽模式。但是,点明反讽的反讽却是刻意而为,由此才能表现一种针对反讽自身的反讽意识的转向。”这种表白意味着,只有针对反讽的反讽,才可能是超越反讽的适当道路。怀特对传统史学及其认识论的讥讽为的是表明,反讽不过是诸种解释模式中的一种,我们用反讽模式来解释历史和用其他的模式来解释都是合理的,至于我们最终选择哪一种模式解释历史,依据的则是美学的和道德的基础。 我们若是将《元史学》当作一部针对19世纪欧洲史学思想史的叙述作品,进而根据怀特在《元史学》中提供的理论,试图在作品本身中寻找怀特所说的那种未经批判便被接受的元史学要素,最终揭示出文本中隐性的更深层,结果我们会看到,一切未知的似乎都早已成了已知的。这是因为怀特告诉我们,反讽便是这种元史学要素。他还进一步论证了反讽的自我批判性质,指出“反讽在一定意义上是元比喻式的”,“在一个探寻自我意识水平的特定领域内,反讽的出现看上去标志着思想的升华”。然而,怀特的理论表述与叙述实践之间的张力并没有因他对反讽的自觉认识而消除,相反,我们却能更明显地感觉到。一方面,如果怀特运用的反讽真正相当于他所分析的那些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文本中的隐性的、未经批判的前提,那么,反讽在此却是显性而非隐性的、是可认知的而非前认知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据此认为《元史学》本身不受它所表述的理论所支配,那么,怀特期望他的理论具有的那种一般性和普遍性意义就不复存在,至少他的理论不能运用到《元史学》中。另一方面,如果不顾怀特对于反讽具有的自觉认识而认为他的理论表述总体上是正确的,他的历史叙述理论中就应该存在一种不同于反讽而又隐藏着的、未经批判的前提。但我们注意到,怀特强调了反讽的元比喻性质,以及将它视为思想的升华,这无异于赋予反讽一种超越隐喻、转喻和提喻的更为优越的位置,排除了寻求某种隐性的更深层的可能性;再者,假使这种隐性的更深层存在,它也应该是怀特本人不能意识到的。就此而言,《元史学》及其阐述的理论的确更像是一种诗性想象的产物。 在历史学领域内,诗性与理性的结合依然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过程,我们只能说怀特在《元史学》中进行了一次积极的尝试。当他强调历史叙述中诗性行为的重要性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角度,认为怀特是在努力对历史叙述中的诗性行为进行理性解释,将它纳入到认识论的范畴中来,因为提出一种理论本身就意味着对原本未纳入到理性认识中的事物进行理性解释。不可否认的是,《元史学》出版之后,它的影响日益增强,到20世纪80年代,以怀特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逐步兴盛,《元史学》提供的多元解释体系更是受到新一代史学家的追捧。更值得一提的是,怀特最初撰写《元史学》是尝试将多学科的最新成果结合在一起构建史学理论的新体系,结果《元史学》不仅将怀特缔造成一位历史哲学的先锋人物,也将他缔造成一位前卫的文学批评家,从这一效果而言,怀特和他的《元史学》真正实现了他在《历史的重负》中表达的理想,将历史学领入了一个新纪元。 在20世纪90年代,海登·怀特还不太愿意他人称其为后现代主义者,而是以结构主义者自居。《元史学》在形式上是结构主义的,但其中的思想却不可阻挡地伸向后现代主义。2004年4月和2007年11月,怀特分别访问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我们在那些时候已经常常听到他自称为后现代主义者了。《元史学》对于传统史学思想的冲击依然在延续。当人们在历史研究中习惯性地运用建构、虚构、叙事、表现、比喻等术语时,他/她或许就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怀特的思想。当然,一种思潮的诞生和扩展不是怀特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但他无疑是其中一位举起火炬、照亮道途的人。 陈 新 2009年3月 中译本前言 海登·怀特 《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在今天,我就不会这么写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认真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 我相信,对于历史作品的研究,最有利的切入方式必须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这种认真程度超过了那含糊不清且理论化不足的“风格”观念所能允许的。那种被称为比喻学的语言学、文学和符号学的理论分支被人们看成是修辞理论和话语的情节化,在其中,我们有一种手段能将过去事件的外延和内涵的含义这两种维度联系起来,藉此,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话语的比喻理论源自维柯,后继者有现代话语分析家,如肯尼斯·伯克、诺斯罗普·弗莱、巴尔特、佩雷尔曼、福柯、格雷马斯以及其他人,它仍旧是我的史学思想的核心,是我对于史学与文学和科学话语的联系,以及史学与神话、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联系这种思想的核心。我致力于把比喻当作一种工具来分析历史话语的不同层面,诸如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伦理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学和形式层面,正是这一点,使得我在如何区分事实和虚构、描述和叙事化、文本和情境、意识形态和科学等等方面与其他史学理论家不同。 比喻对想像性话语的理论性理解,是对各种修辞(如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生成想像以及生成种种想像之间相互联系的所有方式的理论性理解。修辞生成的想像充当了实在的象征,它们只能被臆想,而不能直接感知。话语中(有关人物、事件和过程的)修辞之间的话语性联系并非逻辑关系或与他者的演绎性继承关系,而通常意义上是隐喻性的关系,即以凝练、换位、象征和修正这样的诗学技巧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任何忽视了比喻性维度的对特定历史话语所做的评价都必定无法理解:尽管该话语可能包含了错误信息并存在可能有损其论证的逻辑矛盾,它还能令过去“产生意义”。 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这一传统观念表明,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既然没有哪个被理解为一组或一系列离散事件的事件场实际上能够描述成具有故事的结构,我便采纳了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它,一组事件的叙事化将更具比喻性而非逻辑性。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会更有益。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如果它们不再强求,对于历史话语研究而言,比喻的方法看上去尤其是正当的。 我一直感兴趣的问题是,修辞性语言如何能够用来为不再能感知到的对象创造出意象,赋予它们某种“实在”的氛围,并以这种方式使它们易于受特定史学家为分析它们而选择的解释和阐释技巧的影响。这样,马克思在1848年巴黎起义期间对法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描述为工人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做了准备,他正是用这种分析解释他们在随后事件中的行为。这种在最初的描述和马克思的话语中紧随而来的解释之间获得的一致性是形式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它并不是给“真实的不一致性”戴上了“虚假的一致性”的面具,而是诸种事件的叙事化,这种叙事化展示了时间进程中事件群的变化和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转变。人们不可能将一种实在的事件序列描述得表现出“喜剧”意义,除非他把相关的行为者和事件过程描绘成那些人们能够看作是“喜剧”类型的现象。不同表现层次彼此类比相连而获得的话语的一致性完全不同于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后者中,一个层次被认为是能够从另一个层次演绎而来的。近来人们想要提出一种有关历史因果的融贯学说的努力失败了,这说明科学化的“法则式演绎”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工具是不完备的。 我认为,史学家尤其想通过将一系列历史事件表现得具有叙事过程的形式和实质,以此对它们进行解释。他们或许会用一种形式论证来弥补这种表现,该论证认为逻辑一致性可以充当其合理性的表征和标示。但是,正如存在诸多不同的表现模式一样,合理性也有诸多不同的种类。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对1848年事件的描述很少有“非理性的”,即便其中有许多“假想的”和大量“虚构的”东西。福楼拜以尝试形成一种无法区分对(真实的或想像的)事件的“解释”与对它们的“描述”的表现风格而闻名。我认为,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历经李维和塔西佗,下至兰克、米什莱、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伟大的叙事史学家往往的确是如此。在此,我们必须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那样来理解“风格”:它是某种稳定的语言使用方式,人们用它表现世界,也用它赋予世界意义。 意义的真实与真实的意义并不是同一回事。用尼采的话说,人们可以想像对一系列过往事件完全真实的记述,而其中依然不包含一丝一毫对于这些事件的特定的历史性理解。历史编纂为有关过去的纯粹的事实性记述增添了一些东西。所增添的或许是一种有关事件为何如此发生的伪科学化解释,但西方史学公认的经典作品往往还增添了别的东西,我认为那就是“文学性”,对此,近代小说大师比有关社会的伪科学家提供了更好的典范。 我在《元史学》中想说明的是,鉴于语言提供了多种多样建构对象并将对象定型成某种想像或概念的方式,史学家便可以在诸种比喻形态中进行选择,用它们将一系列事件情节化以显示其不同的意义。这里面并没有任何决定论的因素。修辞模式和解释模式或许是有限的,但它们在特定话语中的组合却是无限的。这是因为语言自身没有提供任何标准,以区别“恰当的”(或者字面的)和“不恰当的”(或修辞的)语言用法。任何语言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都并未遵循清晰的规则来区分某种特定言说的外延和内涵层面。诗人们了解这一点,他们通过运用这种模糊性使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启示性效果。历史实在的叙事大师们也是如此。传统的史学大师们同样知道这一点,但到19世纪时,历史学越来越被一种追求明晰性、字面意义和纯粹逻辑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实现的理想所束缚,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我们自身的时代中,专业史学家没能使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这表明那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近来的“回归叙事”表明,史学家们承认需要一种更多地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的写作来对历史现象进行具体的历史学处理。 这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 我在《元史学》中试图分析的正是这种意义产生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确实,正如人们现在认识到的那样,我当时也认识到,通过进行论证以便“科学地”说明过去或者“解释学地”解释过去,史学家能够赋予过去以意义。但是,我那时更感兴趣的是史学家把过去构成为一个主词的方式,这个主词可以充当科学研究或解释学分析的可能对象,更重要的是,充当叙事化的对象。我认识到,“罗马帝国”、“罗马天主教”、“文艺复兴”、“封建主义”、“第三等级”、“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拿破仑”、“本·富兰克林”、“法国大革命”等等(或者至少是这些术语所指的实体),早在任何特定史学家对它们感兴趣之前就存在了。但是,相信某个实体曾经存在过是一回事,而将它构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知识的可能对象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相信,这种构成行为既与想像相关,也同样和理性认知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一种构思历史写作的“诗学”而非历史“哲学”的努力。 诗学表明了历史作品的艺术层面,这种艺术层面并没有被看成是文饰、修饰或美感增补意义上的“风格”,而是被看作某种语言运用的习惯性模式,通过该模式将研究的对象转换成话语的主词。在史学家探询过去的研究阶段中,他/ 她的兴趣是,就他/ 她感兴趣的对象以及该对 象在时间中经历的变化建构一种精确的描述。他/ 她这样做是以文献档案为基础,从其内容中提取出一组事实。我说的是“提取”一组事实,因为我对事件(作为在尘世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事件)和事实(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做了区分。事件发生并且多多少少通过文献档案和器物遗迹得到充分的验证,而事实都是在思想中观念地构成的,并且/ 或者在想像中比喻地构成的,它只存在于思想、语言或话语中。 说某个人“发现”事实,这毫无意义,除非我们用这种断言指的是在文献中发现的陈述,它们证明了在特定的时空中发生了特定的事件。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在说语言学事件,如类型2的X事件在A时间和Ⅲ空间中发生这样的陈述。这正是我选用巴尔特的话“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作为《话语的比喻》一书的题词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并不是说,“事件”只有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我想要强调的是,在我看来,历史事实是构造出来的,固然,它是以对文献和其他类型的历史遗存的研究为基础的,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构造出来的:它们在文献档案中并非作为已经包装成“事实”的“资料”而出现(可参照柯林武德)。 因此,事实的构成必须像这样以对过去档案的研究为基础,以便充当描述某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如“法国大革命”、“封建主义”、“英诺森三世”等等)的基石,而那些历史现象可能转而又成为说明和解释的对象。换句话说,如果历史说明或解释是一种构造物,是依具体情形观念地并且/ 或者想像地构成的,那么,运用了这些解释性技巧的对象也是构成的。当谈到历史现象时,它也从来都是构成物。 它怎么可能是其他情形呢?只要历史实体在定义上隶属于过去,对它们的描述就不会被直接的(受控的)观察所证实或证伪。当然,通过直接观察所能研究的是证明了史学家感兴趣的过去对象之本质的那些文献。但是,如果这些记载想要不顾事实,而原本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对于可能成为研究主题的对象所作的最初看似真实的描述才得以呈现,那么这些记载就需要解释。这就促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历史知识永远是次级知识,也就是说,它以对可能的研究对象进行假想性建构为基础,这就需要由想像过程来处理,这些想像过程与“文学”的共同之处要远甚于与任何科学的共同之处。 我所说的想像过程是以对意象的思考和比喻性的联想模式为特点,后者乃是诗学言语、文学写作,并且还有神话思想所具有的特征。历史话语中“文学”成分的出现是不是有损于史学所主张的讲述真实以及证实和证伪的程序呢?只有当人们将文学写作等同于撒谎或者歪曲事实,并且否认文学有任何真实表现现实的兴趣时,才会造成损害。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史学归入现代科学,只要人们认为现代科学对确定有关世界的真理不像对确定世界的“现实”那么感兴趣。 的确,我说过,作为创造过程的产物,历史的文学性和诗性要强于科学性和概念性;并且,我将历史说成是事实的虚构化和过去实在的虚构化。但十分坦率地说,我倾向在现代边沁主义和费英格尔的意义上来理解虚构的观念,即将它看成假设性构造和对于实在的“好像”(asif)式描述,因为这种实在不再呈现在感知前,它只能被想像而非简单地提起或断定其存在。欧文·巴菲尔德的著名文章《诗歌用语和法律拟制》对我有所启示,该文指出,在法律上归之于“法人”的“个体人格”就其是某种“虚构”而言仍然是“真实的”。正如前文所述,我始终把“事实”视为建构之物,就是阿瑟·丹托所称的“描述中的事件”,因而在拉丁语“fictio”的词源学意义上,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或话语的虚构,即把它视为某种人工制成的或制作的东西。当然,这正是我看待现代小说中实在表现的方式,它们明显就所描述的一点一滴社会实在都提出了真实性要求,这丝毫不比任何一位进行叙事的史学家所做的弱。关键在于,就叙事为实在强加了那,种只会在故事中遭遇的意义的形式与内容而言,将实在叙事化就是一种虚构化。 史学理论中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由事实而得出的故事是一种浓缩,即将行为经历的时间缩减为讲述的时间,将人们有关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所知的一切事实缩减成只剩那些重要的事实,这种浓缩不仅对特定时空范围内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对于人们就这些事件可能会知道的事实也是如此。将柯林武德所说的史学家“关于事件的思想”转变成(他实际上讲述的或写作的)著述话语,这一行为使用了一切比喻性话语运用中颇具特征性的浓缩和移情。史学家也许想准确地言说,并且只想讲述与他们的研究对象有关的真实,可是人们无法在叙事化中不求助于比喻性语言和比写实性更具诗性(或修辞性)的话语。在特定的过去中,对“发生的事情”所做的纯粹字面的记述只能用来写作一部年代纪或编年史,而不是“历史”。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描述。 因而,如果某人有兴趣构思一部史学史(或历史写作史、史学思想史、历史意识史等等此类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他有兴趣阐明那些在时间中经历的变迁,以及诸种变迁在不同处境下表现出来的差异,而在那些处境中,“过去”已经被解释成了系统性和自反性认知的可能对象,那么,他必然采用一种元史学观点。换句话说,人们不能简单地假定他自身那个时代的史学家(或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是恰当的,也不能简单地以这种概念的循环作为目标,而把令任何事情都或多或少成功地趋向这个目标“从开始起”就变成学科的实践。例如,设想兰克或布罗代尔使用“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历史叙事”,或者“历史解释”(或就此用“文学”、“虚构”、“诗歌”、“模仿”、“过去”、“现在”等等术语)所理解的意思与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用与这些词对应的希腊术语所理解的一样,这没有多少意义,也完全是非历史性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们根据公认的西方史学经典看上去接近或不同于当代史学话语规则的程度,从而对它们做出高下之分,是毫无意义的,并也是非历史性的。 这正是在研究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科学”中的情形,更不用提研究各种非西方形式的“科学”。科学哲学家有充分理由假设,现代物理学家们就有关自然实在的概念提供了有效标准,用来判定在亚里士多德、伽林、普林尼、帕拉塞尔苏斯、阿格里科拉、布鲁诺或培根那里相应使用的观念,近现代科学史涉及的完全是相继的自然因果关系概念之间(并因此而在不同的“自然”或“物理”观念之间)的差异和非连续性,而这些概念曾标志着自公元前6世纪以来“科学”的整体进展。换句话说,一部适当的科学史需要远离和质疑被误认为是我们自己时代的“真正的”科学,以及远离和质疑那种观念的支撑,也即:现代西方科学构成了真正的科学,可以说自泰勒斯或希波克拉底以来,所有其他的科学性观念都为着这一真正科学而努力或是未能成功。如果人们想要形成一种真正历史性的(我的意思是一种真正历史主义的)科学概念,他就必须采纳一种在当前科学正统之外的元科学立场。 译 后 记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28— )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本书便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惟一的专著。本书于1973年出版,至今已逾30年。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西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展示了一种理解史学思想、历史哲学,认识、阐述历史意识发展的新思路,尽管这一思路也是“组装”各学科成就的产物,但它确实为我们思考历史提供了另一种洞见。此外,本书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也有较大影响。其导论曾有学者译出,收入《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王逢振主编,陈永国译)。 1997年,为了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我向怀特索取他的著作,怀特慷慨相助,吩咐出版社寄来此书与另外两本文集。在细读《元史学》之后,我致信怀特,承诺翻译此书,一方面对他的慷慨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这本在我一岁时就出版的著作不再耽误而能尽快被国人阅读。为此,我于1998年联系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赵月瑟老师的帮助下,选题顺利通过,但版权不知何故,迟迟未能解决。2000年,彭刚先生得知我的这一计划,请译林出版社迅速购得版权。从此,我便承担起这一项有些不自量力的任务。 为了实践这一承诺,翻译历时两年有余。虽尽我所能,但毕竟水平有限,译文不免会有错讹之处。此时,特别欣慰的是,有彭刚先生志同道合,他逐字逐句、花费数月校改拙译,做了大量商榷、订正、补漏的工作。另有一事值得一提,在翻译伊始,便有该书另一中文译者刘世安先生慷慨寄赠繁体字译本(译名《史元》,台湾麦田1999年版)。在翻译过程中,每遇疑难,我也参考刘先生的理解,获益匪浅。 译文中,有几个词需要特别说明。 1.realism一词我多数情况下译为“实在论”或“实在主义”,为的是统一译名,遵循历史哲学领域的译法,在本书涉及到文学方面的内容时,读者不妨将此词当作现实主义理解。相应的还有real,reality这类词,较之译“现实的”、“现实”而言,我更多地译为“实在的”、“实在”。此时也请读者不拘泥于我的译法。 2.representation一词我通常译为“表现”,比较另外两种译法“再现”、“重现”,我认为后两种译法易于让人感觉represention指的是“再一次”、“重新”一模一样的呈现,这有违许多当代历史哲学家使用该词的本义,故用“表现”一词,取义类同于艺术表现中的“表现”。 诸多朋友相助,才有今天这个译本,本书历经三校,但一定还有疏漏之处,如果因译文错误导致读者误解,译者自负文责,并敬请读者谅解,不吝赐教,以待来日修正。 近年来,国内对西方历史哲学的译介不多,出于研究的需要,我也忠心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译介这一领域的重要论文、著作,一同促进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理解。 陈 新 2003年11月21日 -
20世纪日本历史学
本书对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史学的演进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反思了日本史学依据何种思想、具有何种问题意识、利用何种方法推进其研究、历史学的趋势与未来等问题。作者并不志在深入描述各个时代、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史的细微内容,而是希望厘清历史学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 全书分为两篇,上篇“近代历史学的形成”从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史学谈起,讨论了启蒙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超国家主义历史观等史学观念与流派的影响;下篇“现代历史学的发展”对二战后至当代的日本历史学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
现代史学的挑战
每年年底,通常在12月28日,美国历史协会行将卸任的主席都要发表一篇“告别演说”。他们或归纳史学界的现状,或总结历史研究的趋势,或阐释本人所关心的具体课题。本书就是1961——1988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说集。 -
新史学九十年
许冠三先生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始致力于史学研究,1974年移席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全心投入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研讨,揭示“多元史络分析法”的治史新途径,在史学界独树一帜。长达四十四万言的《新史学九十年》,则是其多年研究心得的总结,详析“新史学”名家的成败得失,运思深微,立论公允,为近年同类论著所少见。 许冠三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致力于史学研究,1974年起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历史学 -
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
中国社会变化并不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种单向流动的态势所能单独决定的,而是上层政治经济与基层“地方性”反复博弈互动的结果。在西方影响下的上层制度无疑对地方社会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地方社会完全采取被动的姿态,以无法抵抗的无奈形式加以盲从和接受。上层政治制度的形成有时也会在吸收地方传统的意义上调整自己的策略,使之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历史证明,中国近代许多历史态势的形成,都是上层与下层反复拉锯式博弈的结果。可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只是从单向上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而没有把这种动态的复杂性纳入自己的视野,甚至把对传统“政治史”研究的不满直接转换成对下层的研究态度,而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搞明白上层社会的政治运作,也同样很难理解下层社会得以具有所谓“地方性”的缘由。这就是我想重提政治史研究的原因。 -
新史学
本书系美国著名史学家鲁滨孙的代表作,书中作者提出了要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强调历史研究的功用在于通过历史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本书于 1920年代由何炳松译成中文,何氏翻译此书的目的,是认为《新史学》中反映的史学思想,“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针硅”。作为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名著,《新史学》对“五四”以来中国史学现代化建设有着深远影响。 -
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
本书是法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拉迪里的一本代表性著作。 本书综合了社会学、人口学、医学、计量史学的诸多学科的方法,从中世纪法国人口的变化入手,成功地再现了中世纪至近代法国农村社会的重要景象。作者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把历史知识与对事件的观察相结合,从而使史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更清晰。 作者在本书中所作的贡献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震动,在中国同样也得到大师的认同。他的另一本著作《蒙塔尤》被公认为是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本书的出版,可作我国史学界的重要借鉴。 目录 中译本前言 第一章 静止的历史 第二章 一种概念: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14-17世纪) 第三章 扎绳:魔法阉割 第四章 16世纪的法国农民 第五章 巴尔扎克的《乡村医生》简单的技术与乡间传说 第六章 凡尔赛一瞥:1709年路易十四的宫廷 第七章 聚焦鲁埃尔格——纪念雅尼纳·费尔德-雷库拉 第八章 社会为类学家布雷顿的雷蒂夫:18世纪的勃艮第乡村 第九章 危机与历史学家 英文版译者注 小辞典 -
什么是环境史
何谓环境史?它是一种立足于研究不同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理解人类所处、所做与所思的历史。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J. 唐纳德•休斯对环境史所思考的问题、其研究角度与从业者做了全面深入的介绍。他着眼于全球,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形态各异的环境史整合在一起,并揭示了它们各自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与趋势。对这一学科已有深入思考的人能够从本书中获得新的视角;对初学者来说,这本书能为将来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多角度的启发,是一本无可替代的入门教材。 --- 如果想理解环境史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议题以及撰述方法,那么,这本书将以涵盖全球的广阔视野、深入浅出的学术探索以及对前沿成果的良好把握,当之无愧地成为迄今为止最好的向导。—— J. R. McNeill,乔治敦大学 《什么是环境史》是对历史学界一门最重要,也是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学科的权威性概览。它由一位古典学学者撰写,以全球的视野,从容地对古代、中世纪以及当代的环境史进行了考察。对学者们来说,这是一份出色的学术发展水平报告,而学生也可将其用作绝佳的入门指南。—— Sverker Sörlin,斯德哥尔摩皇家技术研究所 -
新旧历史学
本书原名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初版于1987年。在这本书中,作者对20世纪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派和历史写作做了成功的梳理、精湛的批评。所谓的新史学和旧史学并不能确指具体的历史学派和历史研究与协作的方法,因为总会有更多新新史学产生,使原来的“新史学”变成“旧史学”。因此在2004年的修订版中,作者增补进了4篇文章,它们分别论述了后现代主义、世界主义、修正主义和“历史的终结”,阐释了新史学和旧史学的变种。 -
书写历史(第一辑)
历史编撰是科学,还是艺术,或是二者兼之?这是归属历史哲学本体论的一个命题。17世纪,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与意大利美学家、历史循环论的创始者维科,曾先后作出了不同的结论,由此引发了西方史学界长达三百余年的争论。19世纪末,又有人提出要建立历史科学,强调历史学家应该“用精密科学的方法寻找它的事实”。持反对意见者则针锋相对,主张历史编撰要诗化,批评那些缺乏“激情”的史学家不过是历史的“制模工”,不具备“学者的资格”。二战以后,又有人扯起叙述主义史学的旗帜,要以语言文献研究方法治史,直截了当地提出历史编撰是门艺术,让历史学家“向叙事回归”。1973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学》中不仅肯定此说,而且提出了“成文历史”的新概念。他强调:“历史作品以叙事散文的话语作为言语结构”,也就是,编撰历史首先要“当作一种文学形式来处理”,同时,还应对“历史感悟和历史概念的性质和特征”作“重新定位”。显然,怀特对18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恪守在科学规则框架内处理历史编撰问题的治史方法进行了全面质疑。 《元史学》的出版,在西方史学界再次引发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大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美国权威刊物《反思历史》发表了著名史学家G·伊格尔斯的质疑文章以及怀特的回应批评,则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又一次成为“世纪话题”而引起各国历史学家的关注。所不同的是,这次争论已由本体论的历史话语,引申到历史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语言学与诸多学科领域,衍生出历史编撰中的事实与虚构、描述与叙述、文本与背景、意识与科学等众多话题的学术讨论,涉及了“成文历史”在走出中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框架后如何在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下构建治史思维方法、话语约定等史学研究目标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无论是伊格尔斯与怀特的辩论,还是乔·巴雷拉重申历史编撰的“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创造历史与讲述历史》),波兰学者多曼斯卡强调“历史的崇高”在于“史学书写的非审美化”,沃勒斯坦演绎“书写历史”与“虚构故事、宣传、新闻报道”的同质关联,都表现了西方史学家构建新史学的理论创新的探索精神。 可以说,这一“世纪话题”所赋予的意义将当下国际史学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无疑为我国的史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治史经验。 收入《书写历史》(“史学前沿”丛书第一辑)的诸篇经典论文对汉语学术思想界重新认识编撰、阐释中国的历史有着很严肃的启示意义。笔者认为,至少在二个方面可获得启迪。一是新世纪史学研究和理论构建应是开放性的,也就是要自觉地置身于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对传统史学作全方位的反思,对历史感悟、史学概念的性质和涵义的演绎需要贯注学术前沿性的探索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历史文化意识;二是构建史学研究目标(包括史学理论的主体研究及文体书写形式的探索)也应建立在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比较的基础上,在重视成文历史的方法论创新与重建过程中,不偏废历史意识,唯此才能获得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真理标准的共识。 当然,《书写历史》汇集当代西方历史学家对“世纪话题”讨论的最新成果,并不意味着鼓励中国史学研究去照搬西方的史学模式和理论体系,而是提倡重在借鉴和参照。这也是出版“史学前沿”丛书的出发点和归宿。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