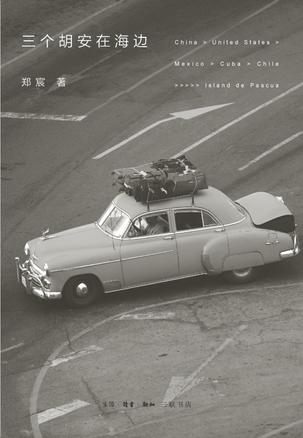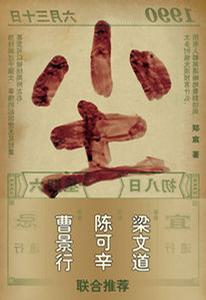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郑宸
-
三个胡安在海边
继讲述印度之旅的《罗摩桥》之后,郑宸又推出南美之旅的《三个胡安在海边》,将他的旅行小说做了系列化拓展。在这部小说中,在以主人公吕伟、何光夫妇去复活节岛举行婚礼为线索,黎成、京昌、艾文、胡安、泰吉、女雕塑家、小平、德国船长……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与心结,在这支旅行结婚的队伍里来来往往,呈现出多元化的群像效果。而他们最终是否能从旅途中找到心灵的慰藉,是否从中舒缓了各自内心深处的苦恼,还需在上海嘉兴、墨西哥、古巴、智利、南极和复活节岛这一漫漫旅途、异国风貌中进行检验。 -
尘
序 南希的出场 打捞海龟的日子 巨变 钥匙的印迹 死在梦中的谁? 一人 中国人? 语言学校 “孩子的家” 最后的拥抱 乞丐的出场 1990年6月30日是原点 另一个老人的手 梦露照片 同学 赤野扶美 哈瓦那 艰难的10英镑 赌博的开始 喘息 乌鸦 叫戮的女人 叫赤野扶美的女人和我的分裂与狂躁 洞的由来 11 空虚的爱人 2008年盛夏的一天 杰夫的短暂告别 自衣圣女 和脱衣舞女孩的第~次见面 黑莲 雅 扶美的伤 Shaleeh和我之间的陷阱 雅的再见 第一次见到雅 雅的名字 陷落也是方向 2004年暑假,秘密的由来 墓在哪里? 藏 引路人之死 7月6日离开金沙萨前往村落前的一小时 Jihad Jihad“朋友”的自豪 诗歌,书店老板 哪个名字? 消失的Jihad 躲儿子的人的儿子 进不去的家门 Jihad的自豪 赤野扶美的最后一次出场 杰夫的战争 杰夫的战争二 2004年11月26日下午四时 2004年11月29日第二次汇看 2004年12月圣诞节假期之前最后一次见面 无法完成的毕业创作 相册和墓 父亲们 急于开始的创作 2005年1月20日开学前三天 难以继续的毕业创作 被安排的春节 毕业典礼 必须被继续的毕业创作 终将离开的窥探者 完成 拥抱 南希的离场 圣马丁的面试 1990年6月30日是结局 试读 南希的出场 “死了?”我忘记了措辞。 电话那边的看护愣了两秒。 “是的,她已经走了,差不多是一周前的事。” “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时问吗?” “……10月20日……” “怎么死的?我是说……死因……” “她离开得很平静,起初还以为是睡着了。”看护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继续说道:“对不起打搅你了,只是我们有义务告知她的亲友,我是说,在这里登记过的。” “……有几个登记过?……” “……只有你……” 两分钟后,我放下了电话。 我的南希,死了。 得知她的死讯后,我没有过分惊讶,预料到的结局。 死讯——那是来自她的结局的恐吓,对我侥幸逃离的不满,显然,来找我的不是南希,是她那孤苦无助的结局。我们曾经相依为命,用对 方的存在对抗看似永远无法战胜的孤单,然而最终,我逃离了战场,她孤身倒下。我深知她永远不会怪责我的离弃与背叛,她甚至会为我感到欢喜,她的笑脸永远那般可爱。然而那不甘心消亡的结局会使出最后的一丝气力让我逃得无法心安理得。而一周来,那不断壮大的不满,聚集 成空前的怨恨,穿过南希的棺木,穿过蜿蜒曲折的空灵公路,穿过阴郁深寒的海峡,穿过冰封高耸的黑色山脉,穿过沼泽满布的草原,穿过被灰色烟尘笼罩的城市……最终,电话响起,在2007年深秋的某夜——我完成学业回到北京后的第十四天。 打捞海龟的日子 我出生在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院子在故宫护城河的北面。墨绿色的生锈的铁门,有门房,过门房十几米左手边是前院,记得有棵枣树,有没有梨树?忘记了,印象中郁郁葱葱什么奇怪的植物都有。还有鸡窝,有狗窝,鸡窝里有母鸡,狗窝里有公狗,后来都被我骑死了。前院有一栋两层的满是爬墙虎的青灰小楼,有天台,不常开,从那里可以看见景山、故宫、角楼和灰色的明天。 院子里有个荒废的泳池,里面的水还在,而且在了很久,一滩黑色的死水,飘满了落叶,时有异味。记得我很怕那潭黑水,不敢接近。 海龟?是哪里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可能是谁送给长辈的,却不明白为何送两只活生生的海龟。 我只见过它们两次,一次是它们来时,一次是死时。 它们来时家人们有说有笑,争先目睹这稀罕物。他们敲打着海龟壳,它们却无法蜷缩,只是挣扎,于是更多大笑着的手去敲打它们,警 卫员的手,锅炉房大大的手……而我只是站在角落静静地俯视着大盆中默然挣扎的海龟,仰视着嬉笑着的众人。终于他们决定把海龟放在落叶泳池里养着,于是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它们。 我曾经小心地靠近黑水,蹲在那里,仔细在无数浮叶的缝隙中细细寻觅它们的踪迹,但是我只是看到了黑色,波光粼粼的黑色。 后来,我忘了,只记得在那个春天我骑死了鸡,骑死了狗。黄狗死时,眼中充满喜悦,鸡死时可能也是,但是它眼睛太小不易确认。 再后来发生的我忘记了,大家都忘记了,忘记了从前,忘记了后来,自然也忘记了泳池里的生物,它们和泳池一起被所有人遗弃了,直到那年夏天泳池散发的臭味比往年大很多,大家才记起它们。 1984年盛夏的一天,曾参与迎接它们的所有人,兴高采烈地开始了打捞工程,他们用几根棍子、几张网捞了很久,依旧有说有笑,而我没去帮忙,只是坐在角落,看着。记得那天很热闹,像过年,家人走出了阴沉的房子,所有家人都在一起,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样的笑…… 两个小时后,雌龟获救了,它被放在了一个盛满清水的大瓦缸里。 半小时后,另一只被捞了上来,它离开水面的瞬间,一阵恶臭,所有人都捂住了鼻子,是那只雄龟,它腐烂了,除了龟壳已经没了形状,黄色的烂肉上沾满了落叶……堂姐吓得跑开了,我没有,依旧默默地看。 之后,我被一只手拉进了阴沉的房子,他们把它们怎么样了?我不知道。 1984年秋天,更多的落叶覆盖在泳池的水面上,泳池看上去成为了院子里地面的一部分。有人在帮助我忘记,只是不知道他想让我忘记什么?他是什么? 1985年,遗弃者填平了被遗弃的泳池,而在同一年,所有的遗弃者被遗弃了。 巨变 家庭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远离了也许从未出现过的美好。所有人都搬走了,而我和父母搬到了很偏僻的郊区,至少当时那里算是郊区,有菜地,数不尽的破旧厂房,路旁杨柳,二十年后那里叫做CBD商圈。我们搬进那里唯一的一座楼房,肉色的它孤单挺立在一片灰黑色的泥沼 中,那是一个陷入泥沼中的裸体男孩。数不尽的窗户是无数呻吟着的口,窗边随风飘起的衣,是那口中的舌,似在召唤着我,压迫感。也许全北京的穷人都住在这里。 实际上四十乎方米的居住空间对于一个三口之家并不那么拥挤,尤其是在80年代,恐怕现在亦是如此。然而对于习惯了奔跑于自家院落中的男孩,它无疑是个丑陋的牢笼。 两个房间。父母为了让它们有家的味道铺上了地毯,一间是红色,暗红;一问是绿色,墨绿。它们是廉价的,但是对于今后的我,廉价而永恒。 家具。父母找朋友在某京郊家具厂用边角料拼凑的:三合板的柜子,三合板的写字台,三合板的床头柜,三合板的一切。价钱低得惊人,低得厂家懒得为他们上漆。于是乎,我们自己找来了别人家用剩下的油漆,凑合着自己为廉价的家具上漆。端详父母为家具上漆的背影,甜蜜是我唯一记得的,我只想记得的。 还记得当时三个人睡在一张旧床垫上,很温暖。 钥匙的印迹 能背下二十六个字母我就可以进小学了,母亲告诉我的。于是为了让自己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有个书读,我无奈地开始背诵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符号,记得背了很久。 谁知道大费周章的背下了二十六个字母后,却换来了一所很糟糕的小学。父母的解释是:那里离家很近,而且便宜。说别的我还可以抗争,而一谈到便宜,我立刻像士兵一样沉默与顺从,我可以说是心甘情愿地去那里读书的,就因为“便宜”,我无怨无悔。 入学的第一天是父亲带我去的,只此一次。 那是一段需要步行二十分钟的路程,绕过几间破平房,穿过一条阴暗狭长满是垃圾、粪便、腐烂树叶的小径。那小径宽不足三米,却很长,是工厂围墙之间的缝隙。抬头,遮天蔽日的树叶,被风带得左右摇摆,光线穿过叶,随风,飘落在垃圾、粪便、腐叶上的光点在不停变幻。父亲在前带路,我紧随其后,还有那些光点,似是一种神圣强大的指引,让我难以抗拒。 那小径如此熟悉,一切像极了十九年后在刚果金雨林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一样潮湿,一样遍布腐叶,一样是遮天蔽日的植被。一墙之隔的工厂里间隔不到十秒就发出的巨响,如同一样可怖的枪声,而我,一样的颤抖。 我们在小径里走了很久,走出去的瞬间也并没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只是感觉由压抑移师到另一处压抑。破烂的民房几近倒塌,密密麻麻的窗子,每个窗都填满了你能想到的所有的廉价日用品和无尽的牢骚、庸碌与盛怒。地是土地,黄土,连一块砖都没有。我们还在北京嘛?我想问。 当然我没有问,只因为那带路者的背影。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留意他的背影,背影不会撒谎。我通过他的背,看到了平日里深深隐藏的愧疚。 处处阴暗,满眼都是私搭乱盖的民房,堆满了各种杂物的煤棚和露天小厨房,摆些旧灶台。 工作时间,人很少。爸爸送我来这趟也是费尽唇舌请了假的。而放眼望去,只见阴影中的几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人,他们在破军用马扎上,零星坐着,没有棋局,没有言语,愣愣的,朽木般,只有他们的眼睛会跟随每一个经过的人转动半圈。他们的眼睛是灰色的,没有黑白。 在最不易察觉的一个角落,蜷缩着一个乞丐,三十岁左右,他没有下肢,至少我看不到,骨瘦如柴,赤裸着上身,脏兮兮地堆在一架不到半尺高的小木车里。他的眼睛倒是黑白分明…… 这是我和乞丐的初会。 继续走了没多远,父亲指着一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说:那就是你的学校。 我愣住了。心中不满,言语归零,这就是当时的我,别无选择,唯有接受。尽管如此,心底的抗争还是存在的,只是瞬间,我下意识地在校门前后退了半步,仅半步,我用最短的时间意识到了自己的退却,止住了。父亲看到,轻轻拍拍我的肩膀,把我推进了校门。父亲说,别把钥匙弄丢了,离开了。我攥着脖子上的钥匙缓慢的走了进去,破旧的木门牌上白底黑字“体育场路小学”。 那和我第一次去到英国一样,前所未有的彷徨。孤单?不,孤单是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去印证的,而我在那两个相同的瞬间,没有意识,只有不知所措,感到自己再次被遗弃了,但不是被父母,而是被生活。那一刻,我将手里的钥匙攥得更紧,因为那是一把可以让我回家的钥匙。 那天我去晚了,新同学,新老师,都列队了,在并不宽敞的操场上举行升旗仪式。所谓操场就是周围无数间破民房的后墙圈起来的。同学无一例外的都是农民儿子的模样,当然还有农民的女儿,再多看两眼,人群中还出现了农民自己。他们看上去的岁数,有些让我想起了锅炉房的大大,他们皮肤多黝黑,脸上大多都有着农民特有的红晕。这农民红的问题实际上困扰了我很多年,甚至在我赴英后,才知道英国的农民脸上也会出现这种界定他们身份的特殊标志。 …… -
罗摩桥
该书是“郑宸旅行图文小说系列”的第一部,讲述了主人公“我”和旅伴“大吉岭小姐”的印度旅行故事。“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的年轻旅行者,沉默腼腆敏感,每天都要通过电话向在国内的未婚妻阿真交流“报喜不报忧”的旅行故事; “大吉岭小姐”是在印度长大的加拿大籍华裔女孩,刚与同性恋女友分手,旅行中她对这片土地既亲近又逃避,极力找寻归属感,却又屡屡受挫……他们带着读者穿行于德里、加尔各答、瓦拉纳西、大吉岭、特努什戈迪……期间路遇贫困的木偶艺人父子、失忆的博物馆管理员、唐人街的华裔企业家、残疾的停车场“狗人”、为儿子筹集“赎金”的司机苟魄、海啸遗孤拉古、索贿的行政办事人员……围绕主人公和各色人物,作者以立场、感情近乎零度介入的客观视角,通过一连串的故事,构筑出一个让人着了魔的印度,一个你不曾听说,从未见过,散发着强烈疏离感的国度——在这个国度,爱情、死亡、家园这三个永恒的主题不可思议地融为一体…… 罗摩桥(Rama's Bridge)是一座传说中连接印度与斯里兰卡的海桥。根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罗摩王子为救被斯里兰卡魔王掳走的爱妻西塔,得到神猴哈纽曼帮助,由猴军花了5天时间筑成罗摩桥,终得深入斯里兰卡杀死魔王救回爱妻。千百年来罗摩桥作为神话故事世代相传于史诗之中,无人提出异议,也无人试图证明其真实与否——直到2002年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002年拍摄的一张航天影像图中清晰地显示出印度与斯里兰卡之间的保克海峡中确实存在着一道狭长的海底沙梁。这一发现,在印度国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它究竟是人造“圣迹”还是自然地貌。 作者选取罗摩桥作为题目,不仅因为它是全书叙事的重要线索,更是想要通过它向读者暗示,这是一部介于纪实和虚构之间的旅行小说——正如罗摩桥,虚实无法考证,全靠细心的读者体味其间微妙的平衡。 2010年2月作者赴印度深度旅行,上山下海入沙漠,足迹遍布印度四方边境地区——原计划16天的旅行,最终用了2个月才完成。这2个月的旅程,为这本小说的故事提供了坚实可信的背景。在书中“我”只是一个过客——受过现代西方教育,但骨子里又有古老的东方情怀,这种“他者”的视角,使得本书对印度的观察要远远超越种种预设的描述和想象。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到印度浮光掠影下的丰富细节,将画面、声音、气味、氛围夹杂着“我”冷静的讽刺和准确的批评呈现在读者面前,真切而富有趣味。 作为一部小说,在对环境的描述之外,人物、情节、对话是《罗摩桥》的重要部分,它们穿插在作者的观察与描述之中,寥寥数笔,“我”的内心矛盾、“大吉岭小姐”的情事、拉古的神秘过往以及所遇到的印度各色人物的形象和个性就跃然纸上,读起来令人兴致盎然。而在书的最后,随着海啸遗孤拉古在隐藏着罗摩桥的海域神秘失踪,所有这些零散、局部的印象、故事最终复合成对作者印度的整体概括和洞察,他在虚实之间苦心布局所要表达的意义也浮出水面——在印度,爱情、死亡、家园这三个永恒的主题是如此不可思议地融为一体。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