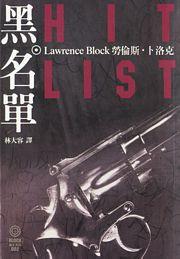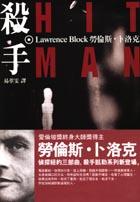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卜洛克
-
别无选择的贼
本書的主角柏納德是個入獄過兩次的賊,他受人委託到一間豪華公寓去偷一個藍盒子。在偷東西的過程中,兩名警察接獲報案前去查看,不料卻發現屋主陳屍臥室,屍體還是溫熱的。柏納德奮力衝出公寓,但卻也從此變成通緝犯。他被迫去證明自己的清白。 -
八百萬種死法
美國當代冷硬首席大師卜洛克代表作「馬修‧史卡德探索」系列,已堂皇進入正統文學的殿堂。 這可能是閱讀情境最接近台灣現狀的一部推理名著:紐約有八百萬人,有八百萬個故事,有八百萬個死法… -
行過死蔭之地
毒梟的妻子被人綁票,綁票的人要求巨額贖金,結果送回來的是毒梟妻子的塊塊屍骨。馬修受命追索兇手是誰,追兇過程中與兇手一路鬥智,甚至仰賴高科技,才順利緝兇。 -
睡不着觉的密探
左擁金髮美女,右抱黃金寶藏,誰還需要睡個好覺呢?鬧鐘......是伊凡•塔納最用不著的玩意。他擁護無望的主張和美女,自從腦子裡的睡眠中樞被破壞之後,就沒睡過覺。而既然聯調局對他緊追不捨,中情局竊聽他的電話,還有個超機密的情報單位想收編他,保持清醒絕對是聰明的做法。 驚人的主張......是塔納最不需要的東西。但當傾國傾城的金髮美女前來求他幫忙,而且還可獲得大批財富的時候,塔納發現自己無法拒絕。然而要將她偷渡入祖國卻是件困難的差事,特別是在同時還得擔心寶藏的時候。更別提還有緊跟在後的執法單位,一步步地趕上他了 溫馨歸國......才是伊凡•塔納最需要的。這是他最初的冒險,由榮獲愛倫坡獎的作家勞倫斯•卜洛克執筆,不可錯過。 -
每個人都死了
《每個人都死了》一書是米基‧巴魯的故事。 米基‧巴魯是地獄廚房葛洛根酒吧的幕後老闆,愛爾蘭裔的職業性罪犯,據史卡德描述,他巨大、凶悍,像花崗岩粗鑿兩下而成的,是活生生的復活島巨人像。 史卡德和他結識於《刀鋒之先》一案中,於是,代表法律的前警員偵探遂和代表反法律的惡徒成為莫逆之交,他們總在葛洛根酒吧坐一整夜,米基喝他十二年的愛爾蘭威士忌,為史卡德準備一壺好咖啡,談到東方既白,再一起到聖本納德教堂望彌撒--史卡德和米基的漫漫長夜對話,一直是史卡德系列中最深沉的一幕。 米基在紐約市裡市外,擁有不少產業和生意,但他的名字從不出現在正式文件上,他說,「當你不擁有,他們就不容易從你手上拿走。」 米基是屠夫之後,他保留了父親遺留給他的屠刀和圍裙,屠刀鋒利如他父親執業之時,圍裙則濺滿昔日的牲畜之血和現在的人們之血,當米基準備動手殺人時,他總會繫上這件染血的白圍裙。他最駭人聽聞的事蹟是,他曾手刃一個名為佩迪‧法雷利的仇家,用屠刀切下腦袋,裝入個保齡球袋之中,並巡行該區所有酒吧,要所有人舉杯祝福法雷利身體健康。 -
殺手
他住紐約,卻無法像史卡德或羅登拔那樣真把紐約當成可深耕密植的家園,生根並且挺身捍衛,史卡德面對死亡暴烈威脅仍不肯遷離,羅登拔花大把銀子買下他二手書店所在的整幢大樓產權;凱勒也沒辦法和固定的人發展綿密杳遠的關係,他選了一個孤獨的行當,就注定得踽踽遵行孤獨之路,他生命中再投緣的人都得從他身邊走開,大概只除了桃兒一個。 性格從不單獨決定命運,我們的人生沒這麼唯心,也從不這麼單純可預料。我們開玩笑說史卡德、羅登拔和凱勒是幼年失散的三兄弟,他們性格的鑄成材料的確也相近(一樣的正直、善良、聰明、世故云云),但他們手中的世界地圖卻不同一張,世界的基本圖像和對應之道遂也大大不同,有點類似萬花筒,一樣的彩色碎紙片,但轉動一下就是不同的樣子。 凱勒是標準的都會獨行俠。他收入好,住在一間不錯的公寓。玩填字遊戲。看點電視。直到電話響起,他理好行李,搭上飛機,飛越半個國家……然後殺掉某人。也是個餬口的方法。然而這叫生活嗎?凱勒不確定。他看了心理醫生,結果出他所料。他找了隻狗,他交了個女友。他活下去。 你從沒碰過凱勒這樣的人。 -
刀鋒之先
「她獨來獨往,可是不常待在她的套房公寓裏。她這麼寂寞能去哪兒?她會去公園,跟鴿子說話嗎?」 史卡德受到委託尋找一個已經失蹤三個星期的女孩,案情毫無進展,這個女孩就像空氣一樣的消失無蹤;同時戒酒協會的朋友艾迪,在滿腹心事來不及說出口的狀況下,被史卡德發現吊死在住處。 她會到哪裡去?他有什麼樣難以啟齒的心事?史卡德能幫上多少忙? 什麼事情都可能會發生,只能期待結果不是太壞。 -
閱讀史賓諾莎的賊
如果石頭有知覺…… 唐诺 這些年來,台灣的本土意識頗為高張,已經到達某種不太講理的地步,讓不少人憂心不已。然而,儘管斑斑歷史告訴我們,這一類國族的、地域的激情容易蔚為某種難以控制的燎原之火,燒傷別人也燒傷自己,但我們對它總容易有種無奈的寬容,相信它有著與生俱來的人性情感基礎,因此很難戒除,也就不好苛責。 麻煩在於,這樣的情感通常總有辦法在自身的歷史記憶之中找到讓自己「長得跟大樹一樣高」的營養材料——儘管在歷史之中,一個國族通常有盛有衰,被別人欺負也欺負過別人(否則老實講也難以存活到今天),但春風得意的往事容易視為理所當然,欺負別人的記憶更是容易遺忘,也因此,每個國族在做這一類回憶時,基本的調子總是滿蒼涼滿充滿不平的,要撐起「做××人的悲哀」這樣的結論沒什麼難的,理由俯拾可得,無須什麼動人的想像力。 比方說,在台灣人怎麼回憶歷史都很悲哀的同時,我們也很難一併想起,那些並非不曉得嘉南平原、蘭陽平原、台北盆地、台中盆地土壤比較肥沃,莊稼比較好成長,因此討生活也比較容易的可憐原住民,何以要那麼辛苦住到不好生活的嚴酷山裡去。 在這方面,荷蘭這個土地面積和我們差不多大、人口密度和我們差不多高的小國顯得很特別。 我個人到過這個國家,印象還不錯,行程中較難忘的除了見識到大麻不管制哪裡都買得到之外,是莫名結識了一位中年男律師,此人極熱情的帶我們去著名的風車區,還在附近一家有名的家庭式鄉村餐廳招待我們吃很好的 pan cake,該餐廳老板的女兒才十七歲,是唯一的女侍,漂亮到一種地步,也害羞到一種地步,同伴中有較不要臉的台灣男性硬邀她合影留念,因此有照片為證—— 自此之後,我再聽得人說荷蘭人小氣,總受人一滴湧泉以報的起身反駁。 我們問律師,英文在荷蘭通行無阻嗎?大律師的回答是,不只英文,還有法文和德文,「我們是小國,靠做生意過活,我們不能期待人家會學好荷蘭語之後才來我們這裡。」——幾年之後,我還聽說荷蘭人有另一種較不正經的講法:所謂的荷蘭語,就是不標準的英文,加不標準的法文,再加不標準的德文。 如果我們以為荷蘭的歷史不夠悲情,因此國族的激情燃不起來,那可就大錯特錯了——荷蘭土地的不幸,除了又小又低飽受大西洋海潮的威脅之外,更要命是它毫無阻攔的正正好擺在德法兩強之間,是天生的好戰場,因此從普法戰爭到一二次世界大戰他們無役「不被與」,像荷蘭的第一大城兼大港鹿特丹,今日看起來仍顯得樹小牆新,便是因為二戰期間幾乎全毀於納粹空軍的轟炸而重建的,荷蘭律師還告訴我們,光是戰役中的一次決堤,便造成了十萬荷人一夕間死去。 而如果我們以為荷蘭人欠缺光輝的歷史遂有受虐虛無的傾向,那也是大錯特錯—— 誰都知道,小小的荷蘭曾在十七世紀雄霸七海,就連相距如此遙遠的台灣也曾在他們轄下,更重要的是,以自由市民自由商人立國的荷蘭,是最早掙開狹隘宗教仇視迫害、思想言論最自由寬容的國家,除了率先貢獻了伊拉斯謨斯這樣的自由無羈心靈之外,更成為理性主義時期歐洲思想家躲避宗教、政治迫害的首選庇護所:它提供理性時代第一人、法國的笛卡爾不受滋擾的思考空間,收容過史上最重要民主啟蒙者、英國的洛克避開政治傷害,並生產出號稱人類歷史上人格最高尚、言行最一致的哲人史賓諾莎(事實上,史賓諾莎的上一代正是因為躲避舊教的迫害,才從伊比利半島遷來的)。十七世紀當時的荷蘭,稱之為歐陸、乃至於全世界的理性燈塔,是半點也沒誇張的。 此外,學美術、喜歡美術的人不會不驚奇於荷蘭畫家的盛產和厲害,一如足球迷對荷蘭告魯夫、古力特、范巴斯頓的驚奇一樣。但這我們留待《畫風像蒙德里安的賊》一書有機會再說——沒有錯,蒙德里安也恰恰就是荷蘭人。 這回,羅登拔先生引述完英國的吉卜齡,開始研讀荷蘭的史賓諾莎起來。 寶化為石 說真的,真不知道他老兄幹嘛要讀史賓諾莎,不管他是賊,抑或二手書店老板,今天除了專業的哲學研究者之外,誰還肯讀史賓諾莎?而就算是專業的哲學研究者,又有幾個人肯好好重讀史賓諾莎呢?比方說寫《西洋哲學史》、可想而知很夠專業的英籍大哲羅素便說過:「讀一讀各命題的敘述,再研究一下評註就夠了。」 乍看起來是因為史賓諾莎的書寫方式——史賓諾莎極可能是理性主義時期最嚴謹、最老實、最徹底到無趣的思想家,他對於把數學的體系搬到哲學甚至神學領域的信心也是最強大的,因此,他寫書的方式幾乎完全仿傚幾何學的體例,有定義、有公理、有定理,在思維之中會發現什麼、會主張什麼,完全是從公理演繹論證而來,不僅讀起來味同嚼蠟,而且,今天我們更已經知道,純粹數學的唯理演繹是走不通的,它的純粹性不是所謂「穿透表象,直指核心真理」的睿智,而是嚴重的化約,因此,得到的結論總是荒謬的。 然而,無關思考和書寫方法,在人類思維歷史的一代代進展之中,個別的思想家本來就存在一種極無奈的宿命。 怎麼講呢?中國有一則八仙之首呂洞賓的寓言故事:相傳有仙人要傳授呂洞賓點石成金之術,呂洞賓不安的問道,石子是否從此永遠轉變為黃金呢?仙人的回答是,不,五百年之後還會回返為石子,於是有絕對主義傾向的呂洞賓遂敬謝不學了——去聖邈遠,寶化為石。 人各有志,這沒得可說的,但今天我們得這麼講,還好人類的哲學家、思想家和諸多理論的建構者,不都是呂洞賓這樣在「全部/沒有」之中二選一、宛若嚮往不容一粒沙子純淨愛情年輕小鬼的決絕之人,否則人類在思維的時間長河之中,大概一步也休想跨得出來,因為,人類思維的進展,原是建立在一代代思維者前仆後繼的錯誤、修正、拆毀重構之上——大概正因為這樣,呂洞賓沒成為皓首窮經的苦學者,而最終成為不食人間煙火、除了遊玩無所事事的神仙。 不記得是哪位學者曾說過如此酸溜溜但頗有幾分真意的話,他說,做為一個理論者,通常 ego 得比文學藝術創作者要小得多才行,原因再簡單不過,你不會不事先明白,你窮盡心血甚或畢生之力才建構的學問理論,只是用來被後人推翻的、用來做為下一個更周延、更進步、更有道理的學問理論發生的必要墊腳石而已。文學藝術,也許不能稱之為永恒不朽,但達到一定的水平之後,它之於時間便有了相當強大的抵禦力量,幾百年甚至幾千年之後的人讀起來,還可以新鮮激烈一如刀劍新發於硎,比方說荷馬、莎士比亞、李白或托爾斯泰等等皆然,不像學問和理論,辛辛苦苦搭建起來彷彿只為了下一次拆毀,說對的部分,很快成為眾人周知的常識,就像今天誰都曉得地球繞著太陽旋轉,不再激得起驚奇喜悅的火花,因而變得像隱形一般,被凸顯被留下的往往只剩講錯的地方,供新的學說新的理論用為反證、或僅僅是誓師出發時祭旗所用。 因此,甭說五百年仍變回石頭,隨著人類智識的普及和歷史律動的不斷加快,往往長則在你身前,短則一年半載,它便轟然倒塌,或更悲哀更常見的,默默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之中。你說,自戀一點的人、自我中心一點的人,怎麼可能明知如此而願意把生命押在宿命的流沙之上呢? 當然,這樣的話也許稍稍自嘲過了頭,歷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及其歷史性的學說或名言,不管正確或說周延與否,其實也很耐得住時間沖刷的,並長期給予後代思維者啟示,比方說笛卡爾和他的﹁我思故我在﹂,比方說萊布尼茲和他的「單子論」;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真的得承認,當時白紙黑字揭示並辛苦論證這些名言和學說的原始著作,可能就乏人問津了,畢竟,要我們假裝自己並不知道幾百幾千年的後續種種,天真無邪的重新費勁跋涉過漫長而乏味的論證過程,最後看到一個我們老早曉得的常識結論,或更糟糕,一個荒唐無稽的結論,這的確不怎麼合於人的基本理性的。 有誰好好唸過笛卡爾的《哲學原理》呢?或是洛克的《人類理智論》和《政治論》呢?這不是挑釁指責,而是調查兼譬喻,如果答案是沒有,想來你也同樣不會讀過史賓諾莎最重要的著作《倫理學》,換句話說,那你比我們的羅登拔先生要理性而且有正事可做得多了。 重讀原典 人壽幾何,書海無涯,儘管如此不合理性,但我個人還是傾向於主張,盡可能還是能讀讀原典的好——這裡的心思挺複雜的,有一點點傻氣,想說至少可對這些為人類攪盡腦汁甚或冒著身家性命危險的思維者表達某種最起碼的禮貌和敬意;有一點點多疑,隱隱約約之間總對歷來的二手傳述者整理者(儘管他們可能也是很棒的學者)有些不盡放心,怕他們難免漏失了什麼,並沒能傳達給我們完整的全相;有一點點好奇,想通過當時的語言和論述焦點選擇,藉此像穿越時光隧道般回到當時,感受理論建構伊始的現實溫度和氛圍;更有一點點希冀和僥倖之心,想說重新涉過原思維者的思考路徑,是不是有可能找到新的啟示火花,或至少讓今天已成不假思索的常識,再次顯現出其豐厚堅實的思維基礎並再現活力來。 如果我們不是那麼計較「投入/產出」的合理性(我個人始終深覺奇怪的是,我們在生活中絕大多數時候並不在意這樣的合理性,為什麼一談到看書讀書時會忽然這麼斤斤計較、這麼要求投資報酬率呢?),即便枯燥乏味如史賓諾莎,也會找到極有意思的東西。 我個人最感興趣的起碼有兩點,一是史賓諾莎所說「凡愛神的人絕不能指望神回愛他」;一是史賓諾莎用石頭譬喻,說「如果石頭有知覺」,它也會認定自己的墜落係出自於自身的意志,由此碰觸到至今仍爭論不休的「決定論/自由意志」的問題。 最虔敬的無神論者 史賓諾莎當然自認,而且後代之人也傾向於相信,是非常虔誠的宗教信徒,他思維的召喚,便是嚴整的、無可懷疑的證明出神的存在(想知道證明過程的人,呃,還是請您自己去唸他的《倫理學》吧),但即使身在荷蘭,他還是因此終身受宗教的迫害,被逐出教會不說,一度還得離開阿姆斯特丹,靠研磨鏡片維生,這固然豐富了他的光學知識,但也因此惡化了他的肺病,讓他只活到短短的四十五歲便安然死去——他的確是非常安詳無懼的死去。 把神的存在都當數學題目來解答的史賓諾莎,他說人不該指望神愛他,當然不是「默默行善不求報償」的道德勸誡,而是,史賓諾莎所揭示證明出來的神,壓根就不會有愛不愛人這回事——淺白一點來說,他的神,其實就是整個自然界本身,不,說整個自然界本身可能還有語病,容易誤解為有相對於自然界、外於自然界尚存在著獨立實體如人為的造物云云,事實上,依史賓諾莎之見,神是全然的無限,至大無外,個別的靈魂和物質並非實體,而是全然包含在神之中,是神的一些表現而已,神既然和人不存在著相對的關係,也就當然沒有愛不愛的問題。 換句話說,史賓諾莎已完全去除了人格神的觀念,連帶的,就連善惡、正義、全知全能等這些相對的、涉及判斷的、有著道德選擇的用語和觀念也全部失去了意義,只剩下井然的、森嚴的、毫無例外的規則本身,正如羅素所講的,「一切事物都受著一種絕對的邏輯必然性支配,在精神領域中既沒有所謂的自由意志,在物質界也沒有什麼偶然。」 在安博托.艾可的名小說《玫瑰的名字》中,做學生的埃森問他的老師威廉修士:「如果說神是全然的自由,那跟說神不存在有什麼兩樣呢?」——史賓諾莎正正好完全相反,但疑問相去不遠:如果說除了神之外,沒有任何的實存,那跟沒有神有什麼兩樣呢? 基督教,不管是新教或舊教,當然忍受不了這個,當然要找史賓諾莎開刀。 這自然有點冤枉,事實上,包括笛卡爾、史賓諾莎等這些理性主義時代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是頗虔敬的信徒(容或程度不一),他們的原意也是想盡一己之力幫忙,畢竟這世界上還有那麼多人不信上帝,有待找出更強力更具說服力的神學理論,而基督教的人格神,不管用做威嚇或勸善,在實踐面的傳教上很有效能,但上千年下來,始終在理論上有著彌縫不起來的矛盾(全能全知的神和人格的神基本上不可能共容,這我們有機會再說),這些思想家都想通過科學的、客觀的論證,一勞永逸的解決上帝存在的問題,他們也自信真的做到了;然而,教會這一頭的不領情也有其道理,當這個上帝不再是《舊約》傳至今天他們所熟悉的那一個,當上帝不再有著傾聽、交流、懲惡揚善、正義審判等等道德性撫慰和勸誘力量,當上帝可以直接用秩序、規律、原理或自然法則來代換,那離無神論也不過是一個跨步之遙而已。事實上,教會的恐懼沒錯,這的確是人類歷史上最急劇除魅的開端,這些想幫忙的思想家,始料未及的一步一步把人帶離開神。 投降的自由 可想而知,在史賓諾莎所構建的這個線條簡單、萬事萬物全依必然規則運行的可怖理性世界之中,一定不可能存在「自由」這高度自主性、選擇性的玩意兒,對吧?是這樣沒錯,但奇怪的是,在《倫理學》一書中,史賓諾莎卻花了整整五分之一的篇幅討論人的自由問題。 也可想而知,史賓諾莎的自由,絕不是今天我們常識理解裡的自由——理由很簡單,如果萬事萬物皆依森嚴的理性運行,不可變易,那麼,能夠調整適應的也只有人自己本身(當然,嚴格來說這也應該是被決定的,不可能有什麼調適問題,但這裡我們就別計較了),因此,這個自由,指的是真切理解不可抗拒規律後的某種心理豁達狀態,而不是外在的選擇權力,以史賓諾莎自己的話來說是,「一個受理性指導的人,遵從公共法令在國家中生活,較之只服從他自己在孤獨中生活,更為自由。」 我們以死亡為例,一個真正理解死亡的必然性,無法因人的意志而改變,從而坦然健康的面對死亡,遠比一個時時憂慮死亡、為死亡所困擾的人,的確要自在幸福,史賓諾莎所謂的自由,指的就是這個。 因此,這個自由基本上是宗教的,而不是政治的社會的,拿來給牧師神父心理醫生勸慰有精神方面困擾的人可能相當好用,但拿到公共領域當一種政治主張卻是極可怕的,這是一種「投降者的哲學」,是集權者要求大家當順民的堂皇說辭,它可以白話翻譯成「法令(某種嚴刑峻法)只有意圖違犯法令的人才會感到困擾,對其他奉公守法的人,法令等於是不存在。」——這不是我們戒嚴時期頂熟悉的、三天兩頭就得聽當權者講一次的話嗎? 因此,史賓諾莎認為人民沒有叛亂的權力,人只能順應,改變自己的心理狀態,讓「自我感覺良好」。 順此,顯然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史賓諾莎用「如果石頭有知覺——」來比喻,說的就是這個。一顆石頭被拋擲出去,它的飛行軌跡和墜落方式,其意志當然出自於拋擲它的那隻手,而不是石頭本身,石頭的自由意志,只是一種自由的幻覺,此幻覺源於無知,源於不知道其背後的推動力量,源於不知道大自然不可逆的森嚴決定性規律。 這個「決定論 VS. 自由意志」的討論,一直貫穿著人類的歷史,至今未休——尤其是後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蔚為洪流之後,它更不再只是抽象的哲學論辯,而是相當程度干係著人類的處境和生存方式,事情變得急迫而且非常大條。 但這裡,我們實在不方便再討論下去了,我只能直接引用當代最了不起的自由大師以撒.柏林的看法以為回應——以撒.柏林以為,決定論假設一種超人類的力量和規律(神或者歷史規則),某種程度上已越出人類的認知和語言所能掌握之外了,因此,它成為某種信仰或選擇,無法用理論來駁斥,但以撒.柏林請相信決定論的人審慎思考,決定論和自由意志完全不相容,而且一旦我們相信了決定論,我們將不可改變的得取消現存所有道德、倫理和法律的用語和觀念,甚至所有比較性的用語和觀念也將一併成為幻覺,沒有善惡、沒有道德責任、沒有高貴與低賤、沒有人的希冀想望挫折反省和懺悔等等,我們將面對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一顆石頭墜落,就像今天台灣中南部山區一下雨常見的,不管它砸死行人,砸毀農舍,截斷道路橋樑妨礙交通,我們不會指責這顆石頭,更沒有檢察官對它提起公訴要它服刑賠償,因為它只是一顆石頭,它的墜落不是自身決定的,不管它是否存著知覺—— 格格不入的賊 這樣的哲學家,這樣一本書,這樣一種看法主張,怎麼會是我們這位自由、看起來也沒像樣宗教信仰、而且一到夜晚就不怎麼奉公守法的羅登拔夫人親愛的小兒子所相信的呢?他幹嘛研讀史賓諾莎? 以我個人對羅登拔的了解,我相信,即使是面對紐約執法當局的逮捕審判威脅,他會做的,仍是努力找出真正該負責任的犯案兇手,讓正義彰顯,而不會援引史賓諾莎式的決定論哲學,告訴警方,我只是一顆被拋擲的石頭,我沒有自由意志,你們該逮捕的是大自然的森嚴規律,是天上那個神,抓祂吧,唸祂的權利給祂聽…… 因為這是個人性尊嚴滿滿的賊。 -
黑暗之刺
九年前,一個瘋狂的冰錐殺手連續刺殺好幾位女性被害人後逃逸無蹤,九年後,紐約警方在偶然的機遇下逮到此人,其他的案件他都承認,唯獨芭芭拉的案子,堅決否認到底。芭芭拉的父親委託史卡德接下這個案子,希望他能找出是誰殺了他女兒。 九年過去,滄海桑田,大部分的人事物都已變化不復當時模樣,「回憶是一種合作的動物,很願意討好,供應不及時,常常可以就地發明一個,再小心翼翼的去填滿空白。」史卡德能找到凶手嗎?他能夠還原事情的真相嗎? -
在死亡之中
傑瑞‧布羅菲爾是紐約警局的警察,他和檢察官合作,以調查警方貪污的真相,他的同僚對此不以為然,但傑瑞‧布羅菲爾認為自己沒做錯。一名來自英國與他從甚過密的妓女,被人發現死在他曼哈頓的公寓裏——他是兇手嗎?史卡德接受委託查出真相,雖然這個委託者他並不樂意接受。(摘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
酒店關門之後
《酒店關門之後》由三個發生在酒店的案件所編織而成,用一本書奢侈的來供應三宗謎題,卜洛克的慷慨還不只如此,事實上,他私心底下更清楚的注目是罪案所在的背景:酒店,和酒店中各色各樣滄桑的人們。 酒店及其人們,在卜洛克筆下,是最精準的紐約風情縮影,一如伍迪‧艾倫鏡頭底下的大紐約街景,做為一個生活於斯、思考於斯、寫作於斯、憂傷困頓於斯的老紐約,卜洛克滿懷眷念的記錄這個集華麗和罪惡於一身的世紀大城。 -
死亡的渴望
我持續探求真相,但是,我發現的東西,實在不值一提。這種感覺在偵探的過程中,其實會一再出現。你敲開一千扇門,問了一萬個問題,只是把片片段段的訊息堆在那裡而已,直到一個線索突然跟另一個線索連在一起,才會頓時柳暗花明。你只能一直往前進,但此時,不斷有聲音在你耳朵邊嘮叨,告訴你,你根本就是白費力氣,在這個當口,要學會充耳不聞。 -
繁花將盡 All the Flowers Are Dying
幾年前丹尼男孩因為結腸癌開了刀,又做了些之後的治療,我猜想是化療吧。這個病讓他明白了自己終有一死,而他的回應方式非常有趣:他製作了一份名單,列出所有他認識而死掉的人。伊蓮問他是不是還繼續在記那份名單。 我已經放棄了,他說,只要時間夠久,我都一直沒復發,我就可以開始相信自己大概擊敗那個混帳病了。不過真正讓我放棄的是世貿中心。雙塔垮掉兩天後,街角那個傢伙,我每天回家路上會跟他買一份報紙,到現在為止有二十年了,結果他現在告訴我,當時他兒子就在北樓裡,他媽的就在被飛機撞上的那一樓。我認識那個小孩,他小時候每星期六都會幫他父親弄星期天的《紐約時報》,把各個版夾成一份。湯米,這他名字。那天我回家,想把他列入我的名單,然後我心想,丹尼,你他媽以為自己在幹嘛?那些人死得快到你都來不及寫下來。 -
蝙蝠俠的幫手
《蝙蝠俠的幫手》集結了十篇馬修.史卡德的短篇探案,從中,你可以回味《酒店關門之後》的故事源頭,可以回到《刀鋒之先》寶拉自17層高樓墜下的現場,還有他和老長官馬哈菲處理一樁舉槍自殺意外的插曲,以及其他各色各樣,揭開馬修.史卡德序幕的原點,是一本進入史卡德、重溫史卡德的最佳選擇。 「我喜歡透過馬修.史卡德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喜歡通過馬修.史卡德的感受來說這個世界。」 ──勞倫斯‧卜洛克 ■本書目錄 窗外 給袋婦的一支蠟燭 黎明的第一道曙光 蝙蝠俠的幫手 慈悲的死亡天使 夜晚與音樂 尋找大衛 夢幻泡影 一時糊塗 立於不敗之地 -
卜洛克的小說學堂
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作家勞倫斯.卜洛克談寫作 看了這本書之後你會發現,原來小說可以這麼讀、這麼寫! 角色開不了口?情節步履沉重?好點子到底打哪兒來?小說家勞倫斯‧卜洛克在《作者文摘》最叫座的專欄,集結成為這本非看不可的作品,深入觀察創作脈絡,告訴你小說如何是一門專業,如何發揮書寫技藝。他的建議,都是身經百戰的經驗之談,讓寫作者可以在創作遊戲中,避開陷阱,悠遊自在。從分析市場開始,到如何自我要求、「創意拖延」,再到處理退稿的失望落寞,《卜洛克的小說學堂》是一本無價的實戰寶典,提供紮實可行的寫作守則,讓讀者與作家都能掌握小說寫作的關鍵所在。 本書獻給 想提筆寫作但不知從何下手的你──這是一本專業寫作指南 想汲取小說家暢銷成名祕訣的你──這是一門越洋函授課程 想一窺出版業界甘苦真實面的你──內含八卦色彩的文壇花絮 想了解卜洛克如何構思敘事的你──真誠深刻的自我作品剖析 幽默風趣的敘事口吻,閱讀輕鬆無負擔 易懂實用的概念技巧,提筆寫作非難事 大師親授的寫作班,開課囉! 或許你第一次接觸卜洛克,是從小說《八百萬種死法》開始。 或許你第一次認識卜洛克,是因為三年前(2005)的訪台旋風。 或許你第一次對卜洛克感到好奇,是因為梁朝偉、王家衛、侯孝賢、唐諾、朱天心、馮光遠、楊照、駱以軍等人都是他的忠實讀者。 唔,或許這是你第一次聽聞「勞倫斯.卜洛克」的大名,那也沒關係。 這肯定是台灣讀者第一次,看卜洛克用一貫的戲謔卻又沉著的文字,談寫作這件事。 「在這本書裡,勞倫斯‧卜洛克很精確的凸顯了創意寫作的方法與道理,功力甚至超過拉和斯‧恩格里(Lajos Egri)的《戲劇寫作的藝術》(The Art of Dramatic Writing)。」 ──布萊恩‧加菲爾(Brian Garfield) 「勞倫斯‧卜洛克是作家的好朋友。他聰明、風趣,實話實說,硬是幫得上你的忙。如果你的朋友無能為力,你的媽媽愛莫能助,就讀這本書吧。」 ──《高爾基公園》作者/馬丁‧克魯茲‧史密斯(Martin Cruz Smith) 「卜洛克在這本書裡所說的話都是「對」的,你可以放心的聽,放心的相信,放心的記得它。方法可能錯誤可能誤導,但技藝沒有成敗,只有進展的遠近程度問題。這也就是說,當你完完全全讀懂了它,也就是你可以丟開它的時候了。」 ──唐諾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