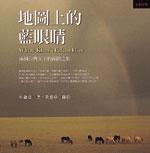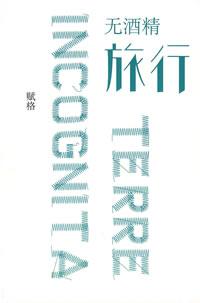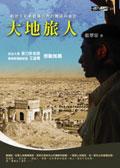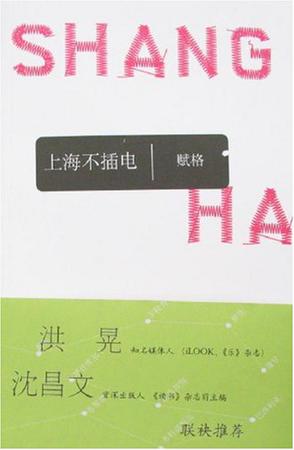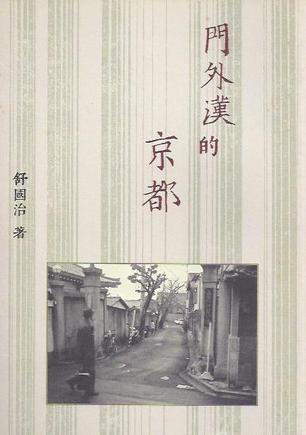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旅行文學
-
柴可夫斯基不在家
這本書是你的眼睛與心靈間的引線,帶領你打開精神故鄉的門扉,看那些藏著天使翅膀的博物館、被神的手指點過的壁畫、神祕而倔強的藝術家故居。這是歐洲最美麗的遺跡,有五顏六色的心靈及無垠的時光、無限的故事,將縮寫在你的眼睛及心裡。到了歐洲,就像芝麻開了門,仙女用神棒點了一下,盜墓人進了金字塔一樣。陳丹燕到了莫札特寫《費加洛的婚禮》的故居;站在柴可夫斯基憂鬱的鋼琴旁邊;站在波提且利畫的嫵媚而茫然的維納斯對面;;在但丁的故居聽人用優美的義大利語朗讀《神曲》;在柏林圍牆博物館流淚;在巴洛克藝術博物館裡快昏過去;在心裡,把漫長的成長夜裡接觸到的歐洲的碎片,一點一滴修補成了一個精神故鄉。 一步,一步,一步,經過一扇門,又一扇門,陳丹燕用十年的時間感受自己和歐洲之間深深的緣分。她用「木已成舟」來形容這樣的心情:「從無數被人類小心收藏起來,認定那是最值得紀念的東西的前面走過,把它們裝進自己的心裡,看這個世界和自己,是怎樣從木變成舟。總是可以感到時間像洪水那樣嘩嘩地淌過去,而孔子在兩千五百年以前,就發過這樣的感慨了。」 作者簡介: 陳丹燕,1958 年生於北京,1982 年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1984 年開始發表兒童文學和青春文學作品,並創作散文、小說。為大陸青春文學第一代作家,也是知名的廣播節目主持人。作品有德、法、英、日譯本。著有《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上海的風花雪月》、《咖啡苦不苦?》、《今晚去哪裡?》等書多部。 與博物館的緣分(自序) 陳丹燕在我成長的時代,中國的門和窗全都被關死,我們只有兩個歐洲友人,就是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家裡的書和唱片已經在我懂事以前全被燒光了,不光是我家的,也是所有別人家的。圖書館裡的書也無法借到,不光是上海的,也是全國的。惟一可以看到的歐洲電影,是《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一九一八》。所有的少年都會說:「牛奶會有的,麵包會有的。」因為瓦西里在電影裡說這句話的時候,一邊親吻著他的妻子,他們的嘴唇因為親吻而變得十分柔軟和靈活。那是少年們看到的惟一的愛人之間的親吻,它深深地激動了一代人,我所在的那一代人。黑暗的七十年代的電影院裡,能聽到一片響亮的嚥口水的聲音。那可真是一個在飢餓中沉睡的年代,九點鐘以後,每戶人家窗前的燈光都暗了下來。 事情總是這樣的,到了八十年代,每一點一滴從西方來的東西,速溶咖啡,畫冊,書,巧克力,音樂,海報,電影,薯片,多種維他命,香水,話劇,鋼珠筆,都一定要像炸彈一樣在我們的生活裡爆炸,年輕的心像宇宙的黑洞一樣無窮地吸入來自西方的東西。惟一想有所選擇的抵制大概來自於我的上海背景,美國的東西的確越來越多,而上海是一個更喜歡歐洲的城市,甚至學英文的時候,都不怎麼喜歡學美國口音,老師更多教的是英國英文。套用一句上海人說香港的話:「香港算什麼,上海是遠東大都會的時候,香港滿街的人都穿木拖板鞋,是個鄉下。」上海人也說:「美國算什麼,歐洲文藝復興的時候,美國還不曉得在哪裡。」在電影展上,當歐洲的電影夾雜在美國電影裡,像餅上的芝麻一樣的時候,去看歐洲電影,就能在電影院裡遇見成群結隊的老朋友,一起看過「麵包會有的」,一起上了大學的,互相抄《歐洲文學史》筆記的,一起在前進夜校上劍橋英文班的。 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東西,不過要找到它們不容易,可是也習慣了這種不容易,這就是我的這一代人吧。 有時候我想,就是因為我這樣長大,才會對歐洲的大小博物館如此熱中的吧。到了歐洲,這種不容易就突然消失了,好像芝麻開了門,仙女用神棒點了一下,盜墓人進了金字塔,我到了莫札特寫《費加洛的婚禮》的故居,站在波提且利畫的嫵媚而茫然的維納斯對面,看到了他當年用刮刀留下來的痕跡,在但丁的故居聽人用優美的義大利語朗讀《神曲》,在柏林圍牆博物館流淚,在巴洛克藝術博物館裡快昏過去,在心裡,把在漫長夜裡的成長中接觸到的歐洲的碎片,一點一滴修補成了一個精神故鄉。十年的時間,幾十個博物館,大到羅浮宮,小到波爾多雪利酒博物館,我像一個螞蟻那樣地為我的精神故鄉工作,因為是先懂得沒有一切的荒蕪,後有了獲得的機會。 一步,一步,一步,從無數被人類小心收藏起來,認定那是最值得紀念的東西的前面走過,把它們裝進自己的心裡,看這個世界和自己,是怎樣從木變成舟。看到義大利的阿萊錯城風蝕了的石頭房子時,想起五百年前喬托筆下的城市,阿萊錯城裡的房子還是新的,總是可以感到時間像洪水那樣嘩嘩地淌過去。而孔子在兩千五百年以前,就發過這樣的感慨了。 用在感受這些東西的時間,十年不算是長的。 我看到自己收集的博物館門票和導覽圖,在地毯上舖了滿滿一地。要不是曾經那樣成長,也許也就不會有這麼深的和博物館的緣分吧。 -
從絲路的盡頭,開始
本書是作者一趟跨越歐亞、走過絲綢之路的真實紀錄,2003年,不論對香港和對全球來說,也是艱苦的一年,戰火和瘟疫,四處蔓延,就在這一年,一位香港女生毅然「離家出走」,帶著僅四千美元的盤纏,背著行囊獨自上路,走過最不為人了解但又最被人所誤解的古老地域,從希臘穿過土耳其安那托利亞高原,來到高加索山三個前蘇聯加盟國,尋訪諾亞方舟和伊甸園的遺跡,再跟著亞歷山大大帝的蹤跡向伊朗邁進,來到南亞的巴基斯坦後,又隨玄奘和法顯的步伐翻過帕米爾高原,到達新疆,踏遍八個國家,渡過愛琴海、地中海、黑海和裡海,歷時七個月。 絲綢之路地段由古至今都是世界上最混亂,最多宗教、種族,甚至是性別衝突和矛盾的地域之一。在2002年,美國向伊拉克宣戰,SARS於全球蔓延之際,作者獨自走上這個誤會重重而又男性強烈主導的地域,以女性的觸覺去觀察、去感受這片土地上的美麗與哀愁,並紀錄著自己與別人在路上的故事。 一個女生獨自跨越歐亞、走過絲綢之路的旅程,觀察到當地生活的真實樣貌,包括蘇聯崩潰後的前蘇聯加盟國,堅守回教基本教義派的伊朗等國,慢慢走過這個古來紛爭不斷卻又風景壯闊美麗的地區。她以一個單身女子的身分,排除萬難,親身體驗當地人民的經濟、文化、風俗、男尊女卑等等,許多讀者難以想像的經歷,接觸同為遊歷者的日本人、台灣人、歐洲人等,也接觸到急欲獨立的庫德族人、懷抱民族仇恨的亞塞拜然人……更親身戴上頭巾,在女性極受禁棝的回教基本教義派國家裡艱難獨行,經歷十分珍貴,並附大量作者親攝精采照片,彷彿帶領讀者親臨現場。 -
地圖上的藍眼睛
本書是兩個台灣女生相約進行一趟絲路之旅的真實紀錄。1998年6月,杜蘊慈與黃惠玲各自背著重達20公斤的行李展開了千里奔馳,她們搭火車穿越戈壁、在蒙古高原上奔馳千里、在貝加爾湖上航行、在西伯利亞鐵路上穿越亞歐大陸、在芬蘭灣旁眺望彼得大帝凝視過的歐洲;走上古老的的絲綢之路,穿越中亞的沙漠、草原及山脈,像千年前的駱駝隊商一樣,往盡集所有絢麗繁華的異國古城前進。一直到11月10日晚上,背著磨損的背包,靴上帶著塵土,兩人回到臺北。習慣了蔽舊的旅館與臥鋪,習慣了三餐不繼,習慣了幾天不能換洗,習慣了陌生的語言與異國的城市,習慣了積雪的高山、乾熱的沙漠、遼闊的草原、湖泊與大河、雨雪與冰川,經歷了歡欣、離別、無助與希望……五個月,穿越陸路2萬7千公里,結束了,兩人回到台灣。書中紀錄了這一切──悠遠、遼闊、歡喜、憂愁與難忘。 -
无酒精旅行
《无酒精旅行》作者自承去过的国家不多(介于 30 到50 个),他对那种插红旗式的统计兴趣缺缺,因为“国家”是一种粗略而不合理的筛孔。作者喜欢的旅行方式是“慢游”,他对边界、边缘人、非军事区格外感兴趣,他致力于描绘“触摸不到的城市”、“第四世界”和旅行者的内心版图─ 山谷,海峡,沙漠,雪原,古代废墟和地震带,拜占庭以及所多玛。 -
大地旅人
2002年,在南方朔眼裡具有古代旅行家特質的「背囊記者」張翠容,將她長達十五年深入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印尼、東地汶、越南等亂世國度,透過記者的鏡頭與文字,全部在《行過烽火大地》裡做了一次最真實的披露,有批判有省思。三年多來,張翠容的腳步從沒停歇過,仍然不時單槍匹馬,遊走在這些紛亂不斷、戰火頻傳的第三世界國家之間。對她而言,別人旅行是度假,然而,她的旅行,卻是為了見證歷史!她的新作《大地旅人》,即是這三年來,再次觀照、凝視行腳過的每個國家、每個城市、每個事件,以及在每趟旅程所遇見過的每個人、所聽聞的每個故事,在經過沈澱、分析、思維下,所抒發的定見及對"記者"角色所應承載的責任與專業的檢視。......在《大地旅人》中,她不僅往外看世界的紛紛擾擾,也向內觀望自身所處的香港現況;一手執握追求真相的判官筆,一手則寫盡在世上每個角落大無畏地貢獻一己心力的無名氏的感人故事。每則簡短的篇章道盡了邊緣國度的慘烈、無奈,可也告訴我們無許許多多令人可敬可愛的人間至情...... -
上海不插电
《上海不插电》是作者过去十年间写作的阅读笔记自选集,除读书读电影读音乐读视觉艺术品以外,也解读个人历史和时代遗迹。作者认为生活与旅行可互相置换,所以书中文字也可看成作者在人生和文本之间旅行的游击。 该书综合了赋格的影评、书评、乐评、摄影作品,以及他在美国的生活经历描述。 他评论《东邪西毒》《2046》,介绍Lonely Planet及其创办人托尼·惠勒,比较张爱玲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指出《艺妓回忆录》的名称误译,谈及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的写作手法; 他欣赏意大利歌曲、英伦三岛古调、舒伯特的小曲、巴赫的变奏曲、莫扎特、赋格、绍兴戏、上海老歌; 他买了普莱斯纳、帕西法尔、凯勒弦乐四重奏团的音乐CD; 他拍摄王尔德的墓碑、旧金山的街头艺术、意大利广场上的马赛克镶嵌、喀布尔的摄影师、开罗的清真寺、罗马的金字塔、伊朗的丝袜。 他在美国搭“灰狗”旅行,逛旧金山的书店,乘旧金山的电车,在 “龙门客栈”打过工,他甚至还坐过美国的班房。 -
流浪集
◆ 流浪 ◎當你什麼工作皆不想做,或人生每一樁事皆有極大的不情願,在這時刻,你毋寧去流浪。去千山萬水的熬時度日,耗空你的身心,粗礪你的知覺,直到你能自發的甘願的回抵原先的枯燥崗位做你身前之事。(摘自〈流浪的藝術〉) ◎人總會待在一個地方待得幾乎受不了吧。 與自己熟悉的人相處過久,或許也是一種不道德吧。(摘自〈流浪的藝術〉) ◎太多的人用太多的時光去賺取他原以為很需要卻其實用不太到的錢,以致他連流浪都覺得是奢侈的事了。(摘自〈流浪的藝術〉) ◎最不願意流浪的人,或許是最不願意放掉東西的人。 這就像你約有些朋友,而他永遠不會出來,相當可能他是那種他自己的事是世間最重要事之人。(摘自〈流浪的藝術〉) ◎須知得道高僧亦不時尋覓三兩座安靜寺廟來移換棲身。何也?方丈一室,不宜久居;住持一職,不宜久擁;脫身也,趨幽也,甚至,避禍也。(摘自〈流浪的藝術〉) ◎行李,往往是浪遊不能酣暢的最致命原因。(摘自〈流浪的藝術〉) ◆ 走路 ◎走路,是人在宇宙最不受任何情境韁鎖、最得自求多福、最是踽踽尊貴的表現情狀。因能走,你就是天王老子。古時行者訪道;我人能走路流浪,亦不遠矣。(摘自〈流浪的藝術〉) ◎要平常心的對待身體各部位。譬似屁股,哪兒都能安置;沙發可以,岩石上也可以,石階、樹根、草坡、公園鐵凳皆可以。(摘自〈流浪的藝術〉) ◆ 喝茶 ◎有時旅行的停歇時機或地點,竟常是因為茶。未必為其美味,乃為其解渴。然而可樂、果汁、礦泉水等亦解渴,何以只特言茶? 這便說到重點。此為茶在某一種微妙感情(家國、歷史、情思、薰陶、年齒………)上最不能教人抵擋之力也。(摘自〈隨遇而飲〉) ◎每日起床,急急忙忙一泡尿。接著如何?便是泡上一杯茶,喝將起來。此外究竟幹得啥事,則不甚記憶。有時想想,人的一生,便在這一泡尿與一杯茶之間度過了。(摘自〈行萬里路,飲無盡茶〉) ◎便因喝茶,判出了一個城市是否宜於人之移動、觀賞、停留。台北市,猶差那麼一點。五十年前的台北,水田廣佈,村意猶濃,光頭長鬚老人與裹小腳老婦猶多,那種時節,樹下稍坐,若有野茶亭,所謂「四方來客、坐片刻無分你我;兩頭是路、吃一盞各自東西」者,倒是頗適合的。(摘自〈行萬里路,飲無盡茶〉) ◎這十年茶喝得多了。比在這之前的三、四十年多得多了。 倒不是這十年懂得品茶,實是比較懂得口渴。(摘自〈隨遇而飲〉) ◆ 睡覺 ◎睡覺,使眾生終究平等。又睡覺,使眾生在那段時辰終究要平放。噫,這是何奇妙的一樁過程,才見他起高樓,才見他樓塌了,而這一刻,也皆得倒下睡覺。(摘自〈又說睡覺〉) ◎倘若睡得著、睡得暢適舒意神遊太虛、又其實無啥人生屁事,我真樂意一輩子說睡就睡。就像有些少年十八、九歲迷彈吉他,竟是全天候的彈,無止無休,亦是無法無天,蹲馬桶時也抱著它彈。吃飯也忘了,真被叫上飯桌,吃了兩口,放下筷子,取起吉他又繼續撥弄。最後弄到大人已被煩至不堪,幾說出「再彈,我把吉他砸爛!」(摘自〈又說睡覺〉) ◎某些遺世孤立的太古村莊,小孩睡得極多極靜,他們的臉格外平靜,是我們都市倉卒之民難以想像之境景。豈不聞古人詩句「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摘自〈睡〉) ◎曾經想過在小說中可用這樣一句子:「睡一個長覺,睡到錶都停了。」(摘自〈睡覺〉) ◎即使是大人,若能讓自己哭,當是睡眠最好的良藥。但如何能哭呢?最好是看感人的電影。(摘自〈睡覺〉) ◎便因熟睡,許多要緊事竟給睡過了頭,耽誤了。然世上又有哪一件事是真那麼要緊呢?(摘自〈睡覺〉) ◎一個十多歲的初中孩子坐在台灣夏日午後的教室裏,室外是懶懶的炎陽與偶有的不甚甘願拂來的南風,室內是老師的喃喃課語,此一刻也,倘他不會昏昏欲睡,那麼他不是個健康簡單的小孩。(摘自〈睡覺〉) 優雅的浪遊 逢甲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張瑞芬 2000年以《理想的下午——關於旅行,也關於晃蕩》驚豔文壇的舒國治,終於在2006年早春,推出讀者引頸企盼的第二本散文集《門外漢的京都》。舒國治的魅力,其實不在題材,而在簡靜的文字與悠閒的意趣。他的旅遊文學屬性,原由1997、1998散文連獲長榮、華航旅行文學獎而來,然而揆諸他《理想的下午》揭櫫的「晃蕩」哲學——「泛看泛聽,淺淺而嚐,漫漫而走」,其實筆下純然是一派安住家居,生活者的氣息,遠非天地遊人的倥傯匆忙。你看他在千年古都尋覓兒時門巷,屋舍寂寂,竹扉半掩,看似舊時台灣鄉下;午夜旅館看黑白老片,猶如60年代台北氛圍重現;夜色中看長牆上孤懸一輪明月,彷彿幼時日本劍道片中場景。簡單來說,《門外漢的京都》猶如家鄉和異地的底片疊合,在他鄉找到了和家相同的質素。場景是京都,可舒國治內心還是那個《台灣重遊》中,趿著拖鞋上夜市擺鹽酥雞攤子的中年歐日桑,很清楚自己是個外人,一點也沒有要融入當地文化的焦灼,反倒有著遠觀的趣味。 這樣的意識,看似遊旅四方,其實台灣在地性格濃厚。世新編導出身,曾經在八年間浪遊美國十數州的舒國治,他的旅遊好比導演到處勘景,聽聲辨位看感覺,屋瓦牆影落日天光都比旅遊指南上的景點重要得多。你瞧他喜孜孜告訴你「京都根本是一座電影的大場景,它一直搬演著『古代』這部電影」;金閣寺別管他的人潮和什麼三島由紀夫了,「只凝視他精緻之極的松、石、島與水上的亭閣」即可。古城三百八十寺,管他收不收門票都只宜張望一下,匆匆經過。某某名剎,簡直的「全寺不值一晒」。明明是玩家也是吃家,他的「門外漢」哲學因此頗有弔詭意趣。放下理性和資訊的焦慮(他甚且不懂日文哩),純任感覺,個人自便,聽不聽也由你。旅館裡的懷石料理繁複精美,吃一口讚一聲,不唯價昂,且工程浩大,實非「尋常像我這樣的阿貓阿狗客人」所能消受;公園旁野餐,川上鶴飛魚游,蘋果熱茶之餘,「倘有幾片cheese,再有一小瓶紅酒,我真他們的想再呆上個把鐘頭」。就像在台北享用高級握壽司後,還非得去啖一碗汕頭牛肉麵,濃重噴香,方足饜飽。住在京都無名小旅店,很像投宿親戚家,「店家的貓在你腳邊看著你換鞋,耳中傳來掌櫃孫女的鋼琴聲」,別有一番情趣。有些人的文字令人欽羨,但也只是欽羨而已,舒國治的文字讓人喜歡,讀者打心裡覺得和他是同類。 舒國治《門外漢的京都》,其實是從《理想的下午》〈城市的氣氛〉一文衍生出來的,無心插柳,展開了一幅淡煙疏雨,留白處處的卷軸。京都古城的旅店長牆、名川美寺,甚至閭巷間的柿果低垂,松枝斜倚,在他筆下無不風情獨具,歷歷如繪。他捨棄厚重綿密的敘述,不貪巨幅,奉行的是「少就是多」、「小即是美」的美學。文字是文言白話的混搭風,雅俗相生,老神在在。〈倘若老來,在京都〉和《理想的下午》中的〈十全老人〉的文言氣,簡直是晚明小品《幽夢影》、《醉古堂劍掃》一路。能讓作家柯裕棻讚譽「內力深厚」、「爐火純青」,可不是太容易的事。楊牧多年前評舒國治得獎小說〈村人遇難記〉就道破天機,說他的文字「聲東擊西」,「看似淡漠鬆弛,實則充滿藝術張力」。《門外漢的京都》中言京都老舊旅店,甬道登樓可聽木頭軋吱聲,進進出出,穿穿脫脫,「此種住店,又豈是住西洋式大飯店銅牆鐵壁甬道陰森與要洗澡只走兩步在自己房內快速沖滌便即刻完成等過度便捷似飄忽無痕啥也沒留心上所能比擬」。這種辨識度極高,誰也學不來仿不像的風格又是啥人可以比擬? 讀《門外漢的京都》,宜把前些時馬可孛羅出版的壽岳章子《千年繁華》、《喜樂京都》翻出重看,一個以千年古風抵拒現代文明的城市,專出那些百年掃帚店、草鞋店、第16代剪刀舖、做榻榻米的頑固老爹。庭園小石步道步步為營,藏青色浴衣有著壓抑之美。和果子店名「嵯峨野之月」、「葛之初花」,女人低首穿著木屐,撐著小雨傘走過長巷。懷念兒時舊事的壽岳章子,和步行晃蕩的外來者舒國治,共築了牆裡牆外的人生。美國小說家愛德蒙.懷特(Edmund White),在《巴黎晃遊者》中說:「晃遊者的定義就是閒暇極多的人」。班雅明更說:晃遊者尋找的是經驗而非知識。浪遊達人的龜毛藝術,豈僅優雅而已。摩挲著《門外漢的京都》一書封面,彷彿聞得到杉木的冷香與質感,如果書本也有氣場,這臥遊便無疑是一場芳美的森淋浴,使人通體適暢。 舒國治的晃蕩,是城市裡恍惚的慢板,優雅的浪遊。從容緩步,以自身經驗為中心,六經皆我(的經驗的)註腳。有著收入《七○年代懺情錄》的〈台北遊藝〉為基底,舒國治的「台北城居」系列,無疑是讀者心中下一個值得期待的人生目標,那絕對是和朱天心各顯神通的另一種漫遊台北的方式。 (原載於《文訊》2006年4月) -
門外漢的京都
「每次得知有朋友要出遠門,將去的城鎮倘我曾經玩過,我總是很多事的想寫下兩三頁紙,上面記著我覺得他應該去玩去看去吃的地點,讓他帶著上路。…… 「我當然也一直想把京都的好玩地點寫在紙上給朋友。這個念頭已有很多年了。一開始我大約會寫下:◎石土屏小路◎宇治川兩岸。沿著川散步,最富閒情。川北岸的「宇治上神社」與南岸的「平等院」不妨只用來當作散步中某一轉折時的點景可也。◎「綿熊蒲鉾店」的甜不辣,如同在台灣所吃之口味,而更勝。◎「茂庵」。開在吉田山頂的木屋式咖啡館。幾次之後,愈寫愈多,如此愈發不易只是兩三張紙了。最後,索性寫成一本小書算了。 「但我仍然希望它像兩三頁紙那樣的隨便、那樣的輕巧、那樣的簡略,以及,那樣的像寫給熟朋友的、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的自在。不知道容不容易做到。」──〈何以寫此書〉 ******************** 一九八三年,二十啷噹的他,推開纔溫熱的copywriter文案,站起身來,舉步出發。 從此再也不曾停下。 幾十年了。 他,總是在晃蕩。 在台灣,在日本,在香港。 從理想的下午漫晃到小食的夜宵, 從西湖的曉風殘月浪蕩去紐約的街巷大道。 他,是六○年代波希米亞的孑遺, 是真正嬉皮精神的延續, 更是浸潤晚明風流的古人在今。 這次,他晃蕩到千年的京都。 他說他是門外漢, 略略一望, 卻盡是巷內人不見的風物景。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