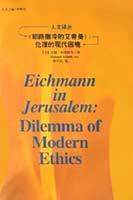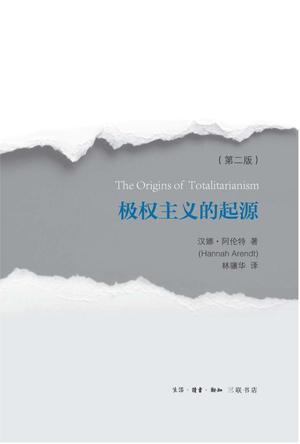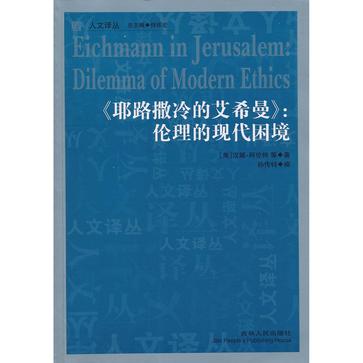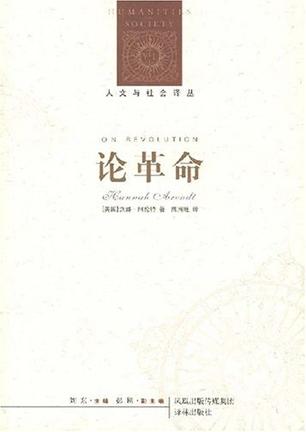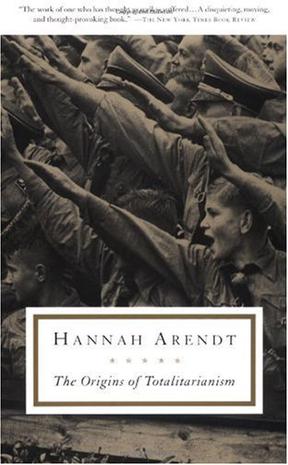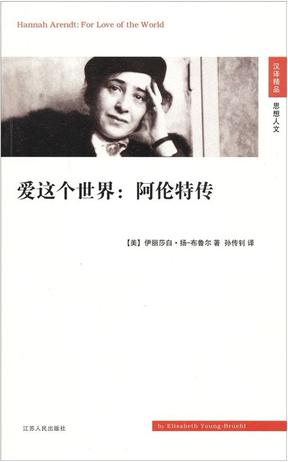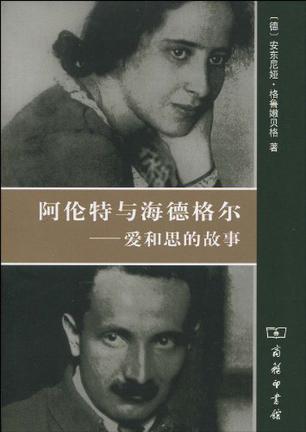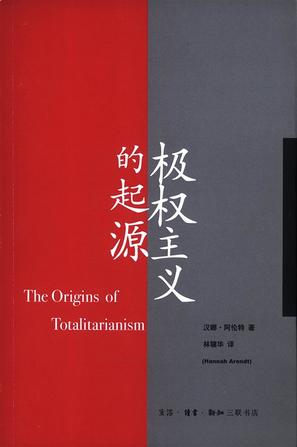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汉娜·阿伦特
-
论革命
简介: “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这是罗伯斯庇尔最后留下的预言;而大西洋的彼岸,美国革命却已经实现了自由的理想。本书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方法和指导两场革命的不同理论入手,深度剖析了两场革命的差异,表达了作者“以自由立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内容围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不同展开:阿伦特不断地比较二者,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偏移,即从“以自由立国”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而美国立国者们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它能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尽管美国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结果却有云泥之别。 导读: 此书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 ——卡尔·雅斯贝尔斯 阿伦特对政治性质的分析体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像她那样给予政治生活的现象学如此多的关注。 ——比库·帕勒克 没有第二个人能像阿伦特那样理解我。 ——马丁·海德格尔 导 言 战争与革命 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但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决定了政治的存在。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了。现代“科学”,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以揭露真相为己任,在它们的合力围攻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起自由的概念看起来更应该安然入土的了。原以为革命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心安理得,甚至死心塌地将自己维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之上:若是缺少了自由的观念,这个传统几乎就无从谈起,更说不上有什么意义。孰料竟连他们也宁愿把自由贬为中下层人的偏见,不愿承认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如果说,自由一词从革命的语汇中消失是那样不可思议;那么,近年来自由的观念卷入当下最严峻的政治争论的暴风眼中,卷入对战争和暴力合理之运用的讨论中,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从历史上看,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现象,而革命,确切说来,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只有在最近的重要政治资料中,方可找到它们。与革命相比,战争的目的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与自由有关。诚然,类似战争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起义,常常会令人感到无比神圣,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被人当成是唯一的正义战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为战争正名,即便是在理论上,也算由来已久,不过它当然不比有组织战争的历史悠久。显然,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信政治关系在正常进程中不会沦落到任由暴力摆布的境地。我们在古希腊第一次发现了这种信念。希腊城邦polis,即城邦国家,开宗明义地将自己界定为一种单纯依靠劝说而不依靠暴力的生活方式(这绝非自欺欺人的空话,不说别的,就拿“劝说”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服毒酒自尽这个雅典习俗来说,足见雅典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免遭肉刑的羞辱)。不过,由于古希腊政治生活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城邦的城墙之外,故对他们而言,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使用暴力,乃是天公地道,不言而喻。他们的外交事务,也只不过涉及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希波战争,看到全希腊都团结起来。在城邦的城墙之外,也就是说,在希腊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之外,“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修昔底德)。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古罗马,以寻找历史上为战争的第一次正名,寻找第一个认为存在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的观念。可是罗马人的区分与正名,都跟自由无关,对侵略性和自卫性的战争也不加任何区别。“必然之战皆正义,”李维说,“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自李维时代起,千百年来,必然性所意味的诸多事情,时至今日,用来给一场战争扣上非正义的帽子,要比冠以正义的帽子更加绰绰有余。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抑或是支持既有的权力均衡——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权力政治现实,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爆发的实际原因,还被认为是“必然性”,也就是说,被认为是诉诸武力解决的正当动机。侵略是一种罪行,只要是抵御或防范侵略,战争就是有理的,这种观点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所具有的可怕杀伤力一览无余之后,才获得了实践的乃至是理论的意义。 在传统上,为战争正名显然不以自由为论据,而是把战争当作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无论何时一旦听说自由被引入了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都会感到极其不快。“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高谈阔论,面对核大战超乎想象的空前杀伤力,不仅沦为一种空谈,简直就是荒诞不经。其实,为了自己国家和后代的自由而甘冒生命危险,与基于同样目的而牺牲全人类,两者之间是那样判若云泥,这就难免让人对“宁死也不赤化”或“宁死也不做奴隶”这些骗人口号的卫道士们大起疑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倒过来“宁可赤化也不愿死”就有多少可取之处。当一条旧真理已经过时,靠头足倒置并不能变得更真实。事实上,今天对战争问题的讨论,还处在这些术语的支配之下,从这一点就不难察觉,双方都是各怀心事的。号称“宁死也不赤化”者实际上在想:损失不会像有些人料想的那样严重,我们的文明会幸免于难;号称“宁可赤化也不愿死”者实际上在想:奴役并没有那么糟糕,人不会改变他的天性,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换言之,此乃诓世欺人之谈,因为双方都在回避自己提出的荒唐取舍;他们并没有当真。 重要的是记住,自由观念被引入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乃是在以下这一点昭然若揭之后: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达到了无法对杀伤手段加以理性运用的阶段。换言之,在这场争论中,自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证明那些以理性为基础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可理喻。难道我们无法将当前令人绝望的纷争硬说成是黎明前的黑暗,称国际关系将会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就是说,甚至不需要国际关系彻底变革,不需要人的心灵和思想发生内在变化,战争就将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会不会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表明我们对战争的消失毫无准备,表明我们要是不提起这一作为最后手段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就没有能力根据外交政策来进行思考了? 除了大灭绝的威胁之外——可以假设,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如一种“无放射性”炸弹或一种反导导弹来消除这种威胁——还有一些迹象指向这个方向。第一个事实便是,全面战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萌芽,那时,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区分再也得不到尊重了,因为它与那时使用的新式武器相冲突。诚然,这一区分本身是较为现代的成就,它的实际废除,只不过意味着战争又倒退到罗马人将迦太基人从地球上永远消灭掉的时代。然而,在现代条件下,全面战争的出现或重现,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假设:保卫平民百姓是军队的功能。政府的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相形之下,本世纪的战争史简直就像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军队越来越不能履行这一基本功能,发展到今天,威慑战略公然改变了军队的角色,使它从保卫者变成了一个滞后的、本质上没有作用的报复者。 国家和军队的关系就这样扭曲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事实虽不怎么惹眼,却颇值得重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就不由产生一种希冀,希望任何政府、任何国家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会强大到可以从战败中幸免于难。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普法战争之后第二帝国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1905年的俄国革命则是随日俄战争的失败而来,这场革命无疑是政府潜在危机的不祥之兆,专等军队失利而爆发。无论如何,政府的革命性变革,不管是由人民自己造成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还是由得胜方凭借无条件投降和战争审判的要求从外部强加的,今天都不外乎是战败最有可能遭致的后果之一——当然,条件是人类还没有在战争中大灭绝。这一事态发展应归咎于政府本身致命的弱化,归咎于权力丧失了应有的权威,还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无论多么稳固、多么得到公民的信任,都经不住现代战争所释放出来的,加诸全体人口的无与伦比的暴力恐怖,这些在本文中都是无关宏旨的。事实上,甚至在核战恐怖之前,战争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还不是在生物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在苟延残喘。 第三个事实似乎指出了通过引入威慑这一军备竞赛的指导原则,战争本来的性质发生了剧变。的确,威慑战略的“实际目标是避免而不是打赢它煞有介事地准备的战争。它企图靠永远不会实施的恐吓,而不是行动本身,来达到目的”。要知道,和平是战争的目的,所以战争是和平的准备,这种见识至少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至于谎称军备竞赛的目的是保卫和平,那恐怕就更古老了,换言之,它与发现宣传辞令的谎言一样历史悠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避免战争不仅是整个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且已经成为军备活动本身的指导原则。换言之,部队不再为一场政治家们希望永远都不会爆发的战争未雨绸缪,他们本身的目标已经变成发展武器来遏制战争。 而且,与这些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努力遥相呼应的是,“冷”战可能取代“热”战这一严峻问题已经浮出了国际政治的地平线。我不愿意否认,也让我们心存一丝希望:现在大国暂时恢复核试验,目的主要在于开发和发明新技术。不过在我看来,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试验跟先前的不一样,它们也充当了政策工具。作为和平年代一种新型的对抗演习,它们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参与演习的不是常规部队对抗演习中一对假想的敌人,而是一对真正的敌人,至少是潜在的敌人。核军备竞赛仿佛已经变成了某种试探性的战争,彼此向对方炫耀手中武器的杀伤力。这场条件和时间都未定的死亡游戏突然间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一天的胜负就可以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这一切绝非不可想象。 这纯属幻想吗?非也。自从原子弹第一次亮相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假想战争,至少是潜在的。很多人那时认为,现在也依旧认为,只要挑选一群日本科学家,向他们演示这种新式武器,就可以迫使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这样一种演示对那些内行人来说就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具有一种绝对优势,靠时来运转,靠其他因素都改变不了。广岛事件过去十七年了,我们对杀伤手段的技术掌控正在飞速迈向这一步:战争中的一切非技术因素,比如士气、策略、指挥官的才能,甚至纯粹的机缘巧合,都被彻底消除,这样就能提前将结果精确地计算出来。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单纯试验和演示的结果对于专家们,就跟以前战场、领土征服和会谈破裂等对于双方的军事专家们一样,都是判断胜负的真凭实据了。 最后也是本文最重要的事实是,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它们的一致性和相互依存性都在稳步增长,而两者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战争转向革命。诚然,战争与革命相互关联,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奇现象,而是和革命本身一样历史悠久。革命要么像美国革命一样,以解放战争为先导或伴随它而发生,要么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自卫战争或侵略战争。此外,在本世纪出现了一类截然不同的事件:对于革命将要释放的暴力而言,战火似乎只不过是一支序曲,一个准备阶段(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对于俄国的战争与革命的理解);抑或相反,世界战争表面上就像是革命的后果一样,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内战,比如,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要根据大部分人的公共意见,以充分的正当理由来看待。二十年后,战争的目的就是革命,能为战争正名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自由而革命,这几乎变成了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无论我们目前的困境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假如我们没有被完全灭绝,与我们一道走向不可预见的未来的,很可能就是革命,有别于战争的革命。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这是一场将今天的世界分裂的竞赛,并且,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岌岌可危。理解革命的人将可能获胜,而那些死抱着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不放,相信战争是一切外交政策最后手段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掌握了一门毫无用处而又过时的手艺。对反革命的精通反击不了,也替代不了这种对革命的理解。反革命一词,是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中创造的,它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就像反动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样。德·迈斯特的名言:“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évolution.”(“反革命不是一场颠倒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这句话从1796年说出之时起,自始至终就是一句风趣的空话。 可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将原本密切相关的战争与革命加以区分,不管多么必要,我们也不可不留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暴力领域之外,战争和革命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事实足以将它们一道从其他一切政治现象中分离出来。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甚至在缺乏任何革命传统的条件下,而且即便以前从未发生过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释放出来的大量暴力,其实已经足以在战后余波中引发革命了。 当然,战争并不是完全被暴力决定的,更不用说革命了。在暴力绝对统治之处,例如极权政体的集中营,不仅法律——就像法国大革命美其名曰的那样,les lois se taisent(法律保持沉默)——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一定要陷入沉默。正是因为这种沉默,暴力成为政治领域的边缘现象。人,就他是一个政治存在而言,被赋予言说的权力。亚里士多德对人下的两个著名定义,即人是一个政治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在,两者相辅相成,都涉及相同的希腊城邦生活体验。此中关键在于,暴力本身是无法言说的,而不单在于言说面对暴力是孤立无助的。由于这一无言性,政治理论极少论及暴力现象,而会将有关暴力现象的讨论留给技术专家。政治思想只能听从政治现象自身的表达,它始终限于人类事务领域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与物理事实相反,它们需要言说和表达。也就是说,它们是某种为了彻底展现出来,从而超越仅仅是物理上看得见和听得见的东西。因此,一种战争理论或者革命理论只能为暴力正名,因为这种正名构成了它的政治界限;如果反过来,这种正名越出雷池,赞美暴力或为暴力本身正名,它就不再是政治的而是反政治的了。 暴力在战争和革命中担当了主角,由此看来,严格地说,战争和革命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即便它们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举足轻重也是枉然。这一事实,使饱经战争和革命的十七世纪走向了一种所谓“自然状态”的前政治状态假设。当然,这绝不是说“自然状态”可以当作一个历史事实来看待。这一假设至今没有过时,就在于它承认政治领域并不会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地方自发地形成,承认在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些事件:尽管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但并不是政治事件,甚至和政治毫无关系。无论我们是按照因果关系,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还是辩证运动的形式,甚至遵循简单的先后顺序,来设想这种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至少间接地指出了一种十九世纪的进步观所无法涵盖的现实。因为,自然状态的假设意味着存在一个开端,开端与它之后的一切泾渭分明,仿佛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开端问题与革命现象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开端,一定与暴力具有内在联系。传说中我们的历史开端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同样,如果没有暴力的运用,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这些在我们的圣经传统和世俗传统中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行为,无论是被人当作传说来流播,还是当作历史事实来信奉,都已经裹挟着一股力量穿越了时代的长河。人类的思想,只有化为贴切的比喻或广为流传的故事,才会具备这样的力量,而这样的情形庶几稀矣。这些故事都是直言不讳的:无论人类能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开端是一场罪行,“自然状态”一词不过是对它进行理论净化的一种释义。千百年来,这一信念对人类事务状态而言,与圣约翰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对于救赎事务而言一样,都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说服力。 -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助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化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
极权主义的起源
《极权主义的起源》的主要分析对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类政治大灾难——极权主义。包括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斯大林的大肃反。极权主义(totalitaf-ianism)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25年,一般认为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人的创造,强调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控制。 -
平凡的邪惡
一本精彩至極,卻絕對令讀者坐立難安的第一手觀察報告! 邪惡…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 理解尤太歷史、納粹德國,甚至正義與邪惡問題的經典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十六年後的1961年4月11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法庭中,展開一場令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審判。審判的主角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在東部佔領區內「尤太問題」的執行者之一,雖然並非納粹政權的高層決策者,但在尤太人滅絕上仍扮演重要角色。 國際著名政治學者漢娜.鄂蘭全程參與此次的審判活動,透過現場的實際觀察,以及對歷史的大量分析,提出了「邪惡的平庸性」的概念。邪惡本身並非得如希特勒般狂暴,而是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並且其發揮的作用絕對不亞於血腥屠夫。本書在1963年出版後,受到廣大注意,也引起許多反彈。但即使經過數十年後,這本書依然是理解尤太歷史、納粹德國,甚至正義與邪惡問題的經典作品。 本書特色 ◎ 本書由東吳大學端木愷講座教授黃默老師審訂、東吳大學人權學程雷敦龢(Edmund Ryden SJ)老師專文導讀。 ◎ 透過政治學者漢娜.鄂蘭的深入分析,顛覆一般對尤太人的既定概念,讓讀者重新思考近代尤太歷史、社會的最佳入門書。 ◎ 對台灣的讀者來說,這本書也更讓我們可以去思考,當一個國家機器假以「公」的名義進行非正義行為時,決策者、執行者、社會群體在公義、在道德、在責任上,該如何去面對。 -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之强制性报告》一书出版后,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本书就以此著及相关讨论为窥镜,希望作现代伦理中一些关乎基准(这些基准是人类良知得以生长的土壤)的思考。 -
论革命
本书围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方法和指导两场革命的不同理论入手,深度剖析了两场革命的差异,表达了作者“以自由立国”的共和主义思想。作者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目标的偏移,即从“以自由立国”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控诉;而美国革命思虑的着眼点一开始就是政治形式的构建,它能确保引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体现更多人或群体的声音和利益。尽管美国革命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结果却有云泥之别。 -
过去与未来之间
阿伦特的笔下勾勒出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紧迫危机:政治学中,诸如正义、理性、责任、德性、荣誉等传统关键词的意义失落,及其带来的后果。通过八篇随笔,她再一次提炼出传统概念中至关重要的精华,以此来评估我们现代人当前所处的位置,重新获致观照未来的框架。 阿伦特对政治本质的分析,体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和洞察力;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像他那样给与政治生活的现象学如此多的关注。——比库·帕勒克 -
责任与判断
《责任与判断》一书完整收录了汉娜·阿伦特生命中最后十年的讲演、报告及随笔,由纽约新学院大学阿伦特研究中心主任杰罗姆·科恩编辑出版,他曾长期担任阿伦特的助手,是阿伦特和布鲁歇尔夫妇遗稿的保存者。 《责任与判断》集中探讨了与恶的本质及道德抉择相关的基本问题,代表性文章为“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回顾20世纪的多重政治危机,其困难和挑战的核心并不在于人们对道德真相的无知,而是道德真相竟不足以作为标准,指引人们作出判断。道德的崩溃反映出的乃是西方思想传统的大断裂。 本书将再次让读者领略到阿伦特思想的渊博与深刻,及其用哲学思考分析当代政治问题的突出能力。 -
反抗“平庸之恶”
没有人比阿伦特更了解:20世纪的道德大崩溃,不是由于人的无知或邪恶,未能辨别道德“真相”,而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评判人们当下可能做出的事情。道德需要重建,而重建道德的前提是社会中的每个个体,能够反抗道德崩溃时代平庸之恶的引诱,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本书收录的文章,主要是艾希曼事件之后,阿伦特对于“平庸之恶”的回应,以及对纳粹犹太屠杀的评论。在这些文章中,阿伦特深入探讨了与平庸之恶相关的政治与道德问题,如“极权统治下的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思考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等。“过去不再启示未来,人心在昏暗之中徘徊”,在人心无所依傍的时代,阿伦特犀利的视角和关切,为我们思考个人处境和选择立场提供了富有启迪的抓手。 本书是《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首收中研院研究员蔡英文专文导读:阿伦特为文一向关注现实的政治与道德的重大议题,文章的肌理糅合了冷静之概念分析与思辨的热情,因而带有相当大的思想激励。 -
人的境况
这部极具原创性的著作,通过对劳动、工作和行动;权力、暴力和体力;地球和世界,以及财产和财富等诸概念的区分,强调了人在面临现代社会高度科技化、自动化和经济现代化情境下,仍然具有的“复数性”和开端启新的行动能力,从而重树人们对于人类事务的信念和希望。这本曾被欢呼为“参与式民主的教科书”,将批判的目光投向我们当前认为理所当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时隔50年,这《人的境况》的原创性仍然像当时一样令人瞩目,并能激发起新的思想和讨论。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definitive work on totalitarianism, this book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any stud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movements. Arendt was one of the first to recognize that Nazi Germany and the Soviet Union we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rather than opposing philosophies of Right and Left. “Wit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nnah Arendt emerges as the most original and profound-therefore the most valuable-political theoretician of our times” (New Leader). Index. -
启迪
本雅明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本书精选了本雅明最精彩的文章. -
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
汉娜・阿伦特与丈夫海茵利希・布鲁希尔的书信同她过去几十年中所出版的众多通信文集[与卡尔・雅斯佩尔斯、马丁・海德格尔等]相比,具有其特殊的地位。没有任何一封信能表现出该书信作者之间这种真诚的信任和理解;所涉猎的话题及人物之广泛,是以往任何书信都难以比拟的。无论是私人话题,还是说艺论道;无论是对大自然的感慨,抑或是对国际政治事件的阐述,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一种挚友般的至诚真情。 正是由于作者间的亲密关系,使得本通信集成为其他出版物的最好补充,是阿伦特遗作中唯一能表现女性的敏感、温柔、依恋的文字记载。这些书信记录了他们三十年间充实的生活经历,让我们看到,夫妇间的爱情是他们在阴霾、险恶中最安全的港湾。 在这本通信集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阿伦特的思想渊源,把握她的思想脉络,认识一个作为学者的她,而且我们还可以生动地认识一个作为人、特别是作为女人的她。作为学者,阿伦特的成就动摇了男性以往在知识界自视的优越地位;作为人,阿伦特是一个诚实、真挚的人;作为女人,她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刻渴求着爱、理解,珍视友谊的人。 -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相遇于1 924年的马堡大学。她那年十八岁,作为一名德国犹太学生在他的班上听课;而他,三十五岁,已有家室。他们的秘密恋情维持了四年,接着是二十年的分道扬镳――在此期间,海德格尔成了一名纳粹.阿伦特移民美国,献身于政治理论和哲学的研究。1950年,两人的关系再度恢复,在一种极为复杂与尴尬的局面下维持亲密友情,直到阿伦特于1974年辞世。 作者爱丁格以大量尚不为人所知的细节,向读者展现了这场奇特的、折磨人的拒斥与缠绵。她告诉我们海德格尔如何在利用阿伦特的同时影晌着她的思想;还有阿伦特如何挣扎着原凉海德格尔尽人皆知的与纳粹的勾结;此外.谁能说海德格尔对阿伦特的爰恋,以及他对纳粹的痴迷,与这名哲人的浪漫倾向没有关联呢? 一个激动人心的爰情故事,一本揭示两位思想伟人的情感世界的书。如果你有志于探询人的内心的复杂,你定会为它所吸引。 -
汉娜·阿伦特:历史、政治与公民身份
这项新研究提供了对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哲学的全新的、及时的重新评价。围绕着对阿伦特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的论述,菲利普·汉森同时向人们展示了她的作品对当代一些政治辩论做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汉森认为阿伦特对什么是政治化的思维以及什么是政治化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论述。在今天真正的政治面临着种种威胁的情况下,这一论述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当代公民理性的基础。 在众多的主题中,汉森着重讨论了阿伦特关于历史及历史行为的观点、她的政治论述以及她对公共及私人范畴之间的区别的论述、她关于极权是最常见的“虚假”政治的分析以及她对待革命的态度。 本书对阿伦特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贡献作了公允的、适时的重新评价,它将受到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哲学学生及学者的欢迎。 -
爱这个世界
与各种理论、意识形态不一样,所有的经验告诉我们,与资本主义同时开始的掠夺过程,其依赖生产资料的掠夺没有结束。只有从经济的各种力量及其自动的特性中独 立出来的法律、政治的制度,能控制、检验这个过程本来具有的各种各样的奇特的状态。若要捍卫自由,只有把统治权力与经济力量分离开来才能实现。 极权主义的各种政府对良心的决定总是怀疑的,是作为一种暖昧的东西来看待的,所以,要压抑有道德的个人表现出来的个人行为。一个人,当被迫选择背叛地杀害友人……等行为时,特别是自杀会就此害了自己家族的场合,应该如何行动呢?这是难以想象的。选择已经不是在善与恶之间,而在杀人与杀人之间进行了。 -
黑暗时代的人们
本书是由传记性质的“人物素描”构成的文集,他们大多是汉娜·阿伦特的同代人及朋友,同她一样经历和见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的不幸和苦难。其中的篇目包括:《思考莱辛——论黑暗时代的人们》(阿伦特1959年获汉堡莱辛奖的致辞)、《罗莎·卢森堡1871~1919》、《卡尔·雅斯贝尔斯》、《伊萨克·丹尼森1885-~1963》、《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1》、《兰德尔·贾雷尔1914~1965》、《海尔曼·布洛赫1886~1951》、《瓦尔德马尔·古里安》等。这些文章体现了作者在洞察世事、了解人性方面的敏锐和犀利,同时,在她的笔下有一种因理解而引起的深情。 -
爱这个世界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之一。她的主要著作《人类境况》、《集权主义的起源》等已经进入西方政治哲学经典的行列。在汉语学术思想界,阿伦特的思想正越来越受到关注。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长达一生的爱情,已超出他们私人生活的范畴,成为20世纪哲学史的一个事件。 此书的内容有:早年生活,渴求知识,献身精神和理性,告别德国,迫害和诽谤,艾希曼以及没有结束,美国的反叛,河面上的光芒等。 -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
1924年,一个学哲学的18岁的犹太女大学生在马堡遇到一位反叛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后来成为纳粹运动的思想先声。于是,在年轻的汉娜•阿伦特(1906-1975)和已婚的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之间演绎出一段激情四射的爱情故事。将近十年后,恰恰是海德格尔寄予民族“觉醒”厚望的纳粹把阿伦特这位德国犹太女性置于流亡境地。她先是逃到法国,最终流亡美国。而海德格尔在短暂出任弗赖堡大学校长一职后,又回到他的哲学中去。1950年,两位主人公久别重逢,旧情复萌,继又开始了关于这个充满破坏的世纪的论辩式对话。 作者在这部关于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双重传记中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巨幅全景。她发掘新材料,向当事人求证。政治巨变及其灾难、崭新的哲学、德国的大学、阿伦特的博士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及其他重要的思想家、美国和欧洲——作者以此为背景,讲述了20世纪最富争议的爱和思的故事。 -
极权主义的起源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作者从19世纪中欧与东欧历史中的反犹主义入手,追索其中的极权主义因素,然后审视欧洲的殖民帝国主义。在研究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机构、组织和运作时,她集中分析了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形式——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结论一章中,她出色地分析了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极权统治的先决条件。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