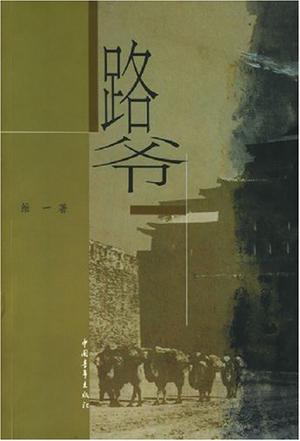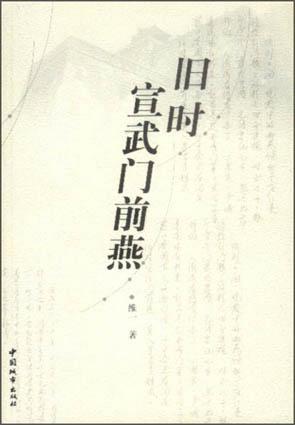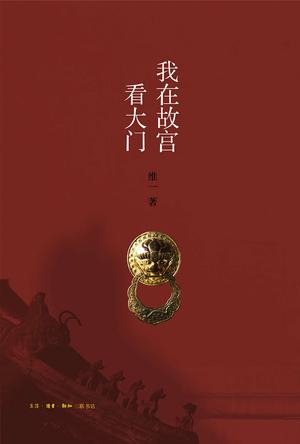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维一
-
路爷
本集《路爷》和年前出版的《旧时宣武门前燕》一样,说的仍然是如今在海外忆想当年京城里的旧事。按说,写作的缘由已经在前一本集子里面交待过了,这里又来一篇《写在前边》似乎多余。 然而也还可以说出个把理由。 一位读过前本集子的读者大约是看穿了我怀旧的情绪,认准我肯定还有尚未渲泄的往事要说,迟早总会行诸笔端,于是他向我建议,时下的世风是连风味小吃和文房四宝都要讲究系列产品,因此我的第二本集子不妨也选定一个系列的标题,一来以求连贯统一,二来也算是顺应时势。 不过我想,主意虽好,但为时已晚。既然第一本集子没有称为“之一”, 何来本集按了排行称为“之二”。 记得幼时母亲带我出门,碰到有父母那一辈尚不十分熟识的朋友,他们一般总会顺口向母亲问起:“这是你家的老几?”意思是指我在家里孩子中间的排行。 当年无论什么都是提倡多多益善,炼钢要一千零七十万吨,种地要亩产万斤,生儿育女也是越多越好。不识时务的马寅初老先生刚刚插了一句嘴,立刻就被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搞得人家灰头土脸。 可惜的是,母亲或许是感到养儿的不易,或许也是恐怕世道的艰辛,总之是响应政府号召不力,只生了我一个。不过母亲倒是十分坦然,遇到这种场合,她便会半开玩笑,半为解嘲地回答道:“他是老大,也是老二,还是老三。”由此看来,如果家中只有一个孩子,便用不到排行。 年前,我将上一本集子的书稿交给出版社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还会有意犹未尽的话要说,所以只是选个书题,既是“之一”,也是“之二”,还是“之三”。 我的想法是,就象是生孩子,早先讲究的是多子多福,如今号召节制生育;写文章也如是,过去标榜著作等身,现在应该提倡少写。道理其实不言自明:从前识字的人不多,为了传播文化,有能者多劳的意思。可是如今社会昌明,识字的人早已遍地皆是,倘若大家都来写,且不说著作等身,只消一人一本书,那全国十几亿人就会让印刷厂日夜开足马力也难以应付。 后来还是听从了一位社会学家多少有些道理的分析我才转了念头。他认为,社会的人口不能忽多忽少,而且人口性别和年龄的比例都需要一个渐进而合理的组成才最为理想,否则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写文章也是如此。他认为,我们这辈人留给后世的记录太少,仅仅才过去十几数十年前的旧事如今已经是鲁鱼亥豕,张冠李戴了。如果我们留下空白,那么只好听凭后世取巧善辩的人信口雌黄。 为了怀旧,信手留下一些文字,倘若因此还能够多少平衡一些由于时代动荡而造成文字记录的比例失调,那么也确实值得一做。既是这样,我便重新打点起精神,把行将停下来的笔再次转动起来,于是又得到以下的二十余篇。 不过集子终于没有如同家中的孩子一般排成“之一”、“之二”。按说倒也不坏,原先在京城里讲究的是按资排辈,如今到了海外,这些规矩还是能免则免了罢。 其实,文如其人,既然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笔,内容尽管不同,体裁到底相近,就象自己的孩子,尽管没有排行,总归是丢不掉的。 -
我在故宫看大门
《我在故宫看大门》作者维一自幼居北京,初中肄业后先到内蒙古农村种庄稼,又到西双版纳农场砍树种橡胶。后来,回到北京闭门读书,到故宫博物院看大门。“文革”结束后,先在北京的研究所和科隆的大学读考古,又到哈佛大学及法兰克福大学访学。《我在故宫看大门》是作者“发掘”自己记忆残片的一组文章,不光是“我在故宫看大门”:“拎在手中的家”因“外事”需要而添置了大衣柜,手摇唱机和好友慷慨相借的唱片,自己组装“无线电”(收音机)的门道,知识青年“扒车”(今天叫“蹭火车”)的道道儿,云南吃马肉的学问,“文革”刚结束时的“内部电影”,淘旧书的荒唐事;还有北京四中的“先生”称谓的讲究,儿时的朋友,王世襄先生的“锡庆门行走”,和张光直先生一起回忆母校的老师,冯爷的外语和学问……一些事,让你喷饭,另一些事,令人心酸。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