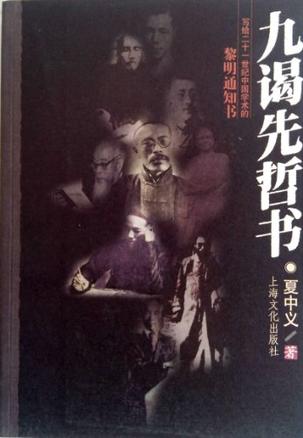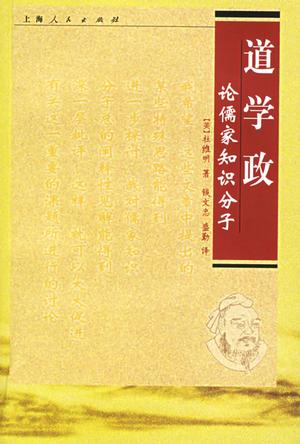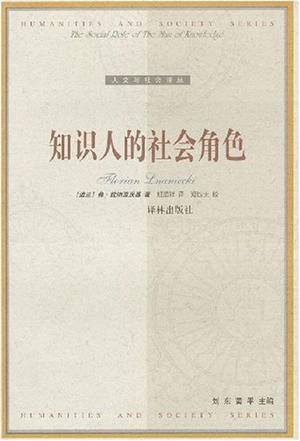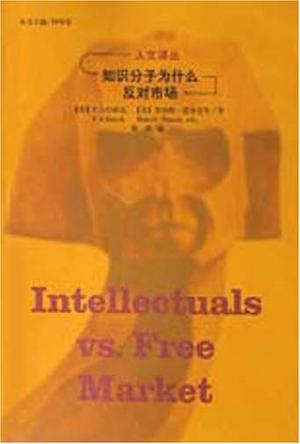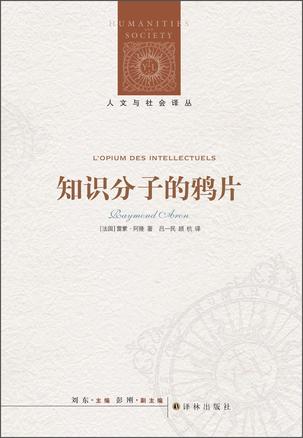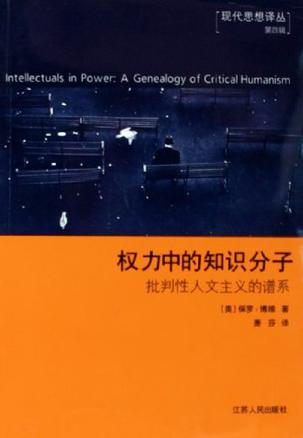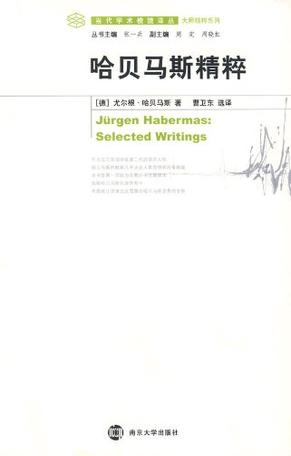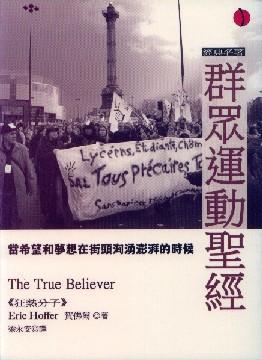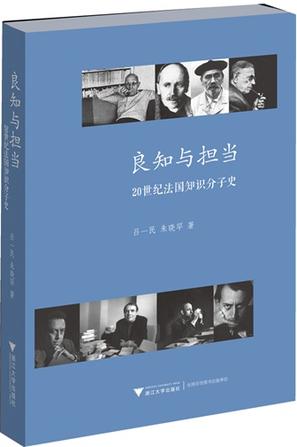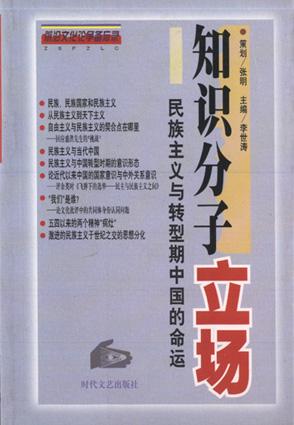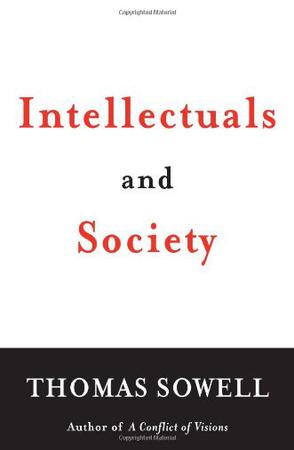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知识分子
-
公共知识分子
这本书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范围进行确定,阐述其类型、形式和风格,阐述了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并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学评论家等进行研究。 -
九谒先哲书
清华园,这片水木清华的土地,当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圣地,曾几何时,它却荒了,野草掩埋着灵地。故当本书依次函谒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胡适、吴晗、闻一多、冯友兰、王瑶等有涉清华背景的三代巨子,这无异于“盗墓暨招魂”,即在发掘百年先哲葬于其间的睿智、傲骨、苦泪、悔悟的同时,又向二十一世纪中国学界喋血呼唤“魂兮归来”,魂即“学统”。 -
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
知识分子的形象常常是混乱的,20世纪知识分子是否对重大事件并由此对国家事业中的勇士,还是堂吉诃德式不负责任、三心二意的人物?甚至是社会骚乱的根源和国家解体的起源?本书通过对法国20世纪历史中最为动荡的几个时期的研究和知识分子参与国家生活的曲折经历的描绘,客观、冷静地评估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影响。知识他子的历史也是观察历史的一扇敞开的窗户,字里行间显示出伟大的法兰西激情。 -
道、学、政
本书是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有儒家知识分子研究的著作,收录的定他学术地位的九篇论文前四篇探讨古典时期的概念体系,标明儒家知识分子的神趋向;中间3篇考察宋元明清新儒学纪元的面貌;后两篇对统儒学的现代意义的思考。从本书中可以窥见作者在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厚功底,极其可贵的是:作者是使用现代西方的方法和话语来重新整合传统儒学的,所以很有新意,作者的思考和表述乏精彩之处,品评人物也十分中肯,少偏颇之处。本书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能给你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 本书所收九篇文章分成彼此关联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古典时期的概念设置和象征资源,集中讨论道、学、政的观念,重点则在标明儒家知识分子总的精神趋向的道德形而上学,孔子及其弟子所体现的核心价值通过修身与为已之学,为儒家纪元的伦理打下了基础。第二部分包括有三篇文章,是走进儒学纪元的知识远足,从意义深远的不同阐释方法的角度,具体描绘了儒学的面貌。新儒学袭用了古典儒学遗产,其中蕴含的多元主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通过作为公共行为的自我努力,有可能改变人类处境的儒学信仰。 -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简介: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具有与《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相媲美的价值。它所播下的种子已经茁壮成长。……本书可能是最具持久广泛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刘易斯·科塞 导读: 一九六八年版导言 刘易斯·A.科塞 一本富有创见却长期被忽视的著作《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重新出版了,作为两个不同国家(波兰和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奠基之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理应获得这一殊荣。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在他的祖国波兰,社会学还没有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兹纳涅茨基几乎单枪匹马,创立了经验研究的传统,对农民和工人的自传体生活史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创建了波兰社会学研究所,创办了《波兰社会学评论》杂志。兹纳涅茨基及其学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成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是目前波兰社会学飞速发展的基础,倘若没有这些,社会学在波兰的发展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一九四○年直到一九五八年逝世这些时间里,兹纳涅茨基都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发现了一门业已繁荣发展的社会学学科,并与一些重要人物特别是威廉·I.托马斯(WilliamI. Thomas)亲密合作。他对成熟的美国社会学传统作出了如此独特的贡献,以至必须同时称他为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 兹纳涅茨基生于一八八二年,那时的波兰,他的出生地还被德国人占领着,他的父亲具有上流社会的血统,当他还是几岁的孩子时,他的父亲把财产耗费殆尽,后来在俄国占领波兰时只是作为财产经营者度过余生((有关传说材料与参考书目主要取材于海伦娜·Z.洛帕塔(HelenaZ. Lopata)教授——她是兹纳涅茨基的女儿——为她父亲的遗著《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Roles,San Francisco:Chandler, 1965)所作的序言。))。在历经华沙、日内瓦、苏黎世、巴黎和克拉科夫的大学学习之后,兹纳涅茨基一九○九年在克拉科夫获得博士学位。他选择的研究领域是哲学,因而第一批著作都是有关这一领域的,尽管他已经显示出对伦理学的社会根源具有强烈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兹纳涅茨基遇见了W.I.托马斯。托马斯来到波兰,研究波兰农民在本土的生活背景,这一课题与他对美国的波兰移民所作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有关。托马斯力劝兹纳涅茨基去美国帮助他完成这项研究,他们之间的亲密合作结出了硕果,出版了不朽名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W.I.托马斯和F.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e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5 Vols, Boston: Badger, 1918—1920)。)),即使在美国,这也是第一项重要的经验性社会研究。理论导向与新奇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之间创造性地交相辉映,使这本书成了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美国社会科学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名著之一。 自从与托马斯合作之后,兹纳涅茨基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兴趣从哲学转向社会学。然而,他在哲学方面的系统训练,尤其是价值理论,明显地反映在社会学著作中,任何读者都可以察觉出这一点。兹纳涅茨基勤于劳作,极其多产。我无法一一涉及他以波兰文发表的九部著作,或用波兰文写成的大量文章。在用英文写成的九部书中,除《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以外,《社会学方法》((NewYork: Farrar & Rinehart, 1934.))、《社会行动》((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36.))和《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可能是最具持久不衰影响力的几部书。 虽然这些著作,尤其是《社会学方法》在某些方面对现代读者来说不免显得有点过时,但在重读它们时,大部分内容给人以深刻印象,在经受住时间检验的程度上尤其令人惊讶。比如,早在三十年代初,兹纳涅茨基在研究社会角色概念时就采用了精致复杂的方法,这应使那些认为社会角色概念是拉尔夫·林顿(RalphLinton)最早于一九三六年提出来的学者们惊叹不已。((R.林顿:《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1936)。)) 兹纳涅茨基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一直坚持认为: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社会学应该集中精力研究行动者赋予情境的主观意义,行动者在情境中发现自身。有人推测,由于兹纳涅茨基早期对于社会价值的调查研究,即使在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似乎要统治社会学领域时期,他仍坚持认为,“科学家要想以归纳法研究[人类]的行为,必须把这些行为看作是人类对于那些作用因素与被作用因素的经验过程;这些因素是科学家的经验材料,只是因为这些因素是他们的”。 ((《社会行动》(SocialActions),第11页。))W)〗在兹纳涅茨基看来,文化材料有别于自然材料,因为后者独立于人类行动的经验,而前者具有“人类相关性”(humanistic coefficient)。在强调社会学调查研究的中心是主观意义、目标搜索和人类行为者的“情境定义”(definitionof the situation)这一点上,早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行动的结构》((New York: Free Press,1949; 第一版,1936年。))得出类似结论之前几乎二十年,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就作出了恰如其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而兹纳涅茨基和帕森斯在概念化方面的一些共同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狄尔泰(Dilthey)和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传统。与其他社会学家相比,兹纳涅茨基和托马斯熟练地利用了詹姆斯(William James)、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杜威(JohnDewey)和库利(Cooley)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成果。他们两人形成了社会学研究中资料整理的理论框架,这种框架成为当代研究与理论的基础。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充分运用了作者过去的研究成果,但目的有点不同。这本书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大贡献,这一社会学分支大致可以定义为研究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九四○年兹纳涅茨基出版此书时,美国社会学刚刚开始吸收二十世纪两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和卡尔·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早期马克思和杜尔凯姆对这一领域的贡献也开始对美国学术界产生影响。((对知识社会学史所作的更全面介绍,请参见L.A.科塞:《知识社会学》,载于科塞与伯纳德·罗森伯格(BernardRosenberg)著的《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 Macmillan, 1957);和科塞:《知识社会学》,载于《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虽然知识社会学的鼻祖或许可以追溯到弗兰西斯·培根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但系统的知识社会学却植根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国的杜尔凯姆传统。 为了把黑格尔的泛逻辑体系倒置过来,也就是说,为了证明这样一个真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相反,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K.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A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Kerr, 1904),第11—12页。)),马克思提出了思想领域是完全由其他因素决定的。按照这种观点,观念系统依赖于其拥护者的社会角色与地位,尤其是阶级地位。马克思断言,某一时期的永恒真理和被人接受的教条必须在最终的分析中被理解为其拥护者阶级地位的表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曼海姆开始自觉地把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学科加以阐述时,他把自己置于马克思传统之内,尽管他实际上还受到了德国历史学、现象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但他在一个关键性的地方有别于马克思:在马克思那里,追溯观念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作为挫败敌手主张的论战性武器,曼海姆却力图使知识社会学成为一种科学的、中性的分析工具。他主张所有观念(不仅是敌手的观念)都与观念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也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事实倒是,每一位思想家只从属于特定的社会集团,占据一定的位置,并扮演专门的社会角色,因而必然影响他据以探讨经验世界的观点与洞察力。所有思考活动都受社会存在决定,或者至少说相互决定。观念“定位”于社会过程之中。现代世界舞台上各种相互斗争的观念,都表达了各自群体和阶级的愿望。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思想立场与结构—历史位置的经验相关性。 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位德国创始人马克斯·舍勒,只是在表层结构上受到了马克思传统的影响,而曼海姆却如此广泛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舍勒是现象学学派的门徒,虽然他是一位异端分子,因而,他感觉到在观念产生过程中预先设置阶级因素是多余的,他反对这样做。相反,他认为,用常驻不变的独立变量(如阶级地位)不可能说明可变的各种观念的出现。舍勒说,若干“真正的因素”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决定着特定的思想产物的出现。在现代社会,阶级因素的确若隐若现,血缘关系曾经是原始社会的独立变量,政治因素在现代社会曾经处于中心地位。进而,舍勒认为以前的理论建立过程中相对主义过于泛滥,他也反对这么做,他试图采取一条恰好相反的道路,因而断言,虽然只有当先决条件“真正的因素”帮助打开思想之流的“闸门”时,特定的一系列观念可能真的会涌现出来,但所有这些观念只不过是向永恒的柏拉图王国中不变的绝对本质投以一瞥而已。 在关于思想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曼海姆与舍勒各自构成了重要部分。相比之下,作为法国知识社会学先驱的杜尔凯姆,关于这一课题所论不多。杜尔凯姆的著作带有模糊不清的认识论思辨,因此比德国人受到更多的诋毁,尽管如此,必须认为,杜尔凯姆的著作是此领域中最关键的开创性研究之一。 在他继续向对社会行为作心理学和原子论解释开战的过程中,杜尔凯姆走进了知识社会学领域。他试图确定道德、价值和宗教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功能,并把道德、价值和宗教解释成为不同形式的“集体表现”(collectiverepresentations),而不是个别思想家沉思的产物。杜尔凯姆并不满足于把这种或那种具体的观念系列追溯到社会历史环境就止步不前,而是主张思想这一基本概念尤其是时空概念是社会创造物,以此力图推翻康德所强调的不变的普适的人类精神范畴。杜尔凯姆断言,社会通过形成逻辑思想据以产生的范畴而在逻辑思想的发生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他认为,对原始人进行时间上或其他的分类,非常接近于对部落的社会组织所作的分类。第一个逻辑类是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中的其他物体,按照部落属性、血统或家族群体加以分类。年代划分对应于周期性的节日和公众仪式,以便让日历能表示集体活动的节律性。按照类似的方式,社会组织一直是空间表征的模型,而天国只不过是它的尘世伙伴的一个投影。在杜尔凯姆看来,所有的象征性思想,都导源于社会组织。 如果有谁想探讨一下兹纳涅茨基这本书的所有思想先驱,那么还必须考虑许多其他成果,这些成果也对三十年代后期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社会学作出了贡献。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斯、杜威,尤其是米德均在此列。然而,在这里我乐于指出(即使最粗略地),他的前驱者的研究方法为兹纳涅茨基设置了一些陷阱。 兹纳涅茨基认为,大多数先前的理论建构有一个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假设强烈地干涉据称是社会学研究的实质性领域。当知识社会学想把自身变成一种“知识的社会学理论”时,兹纳涅茨基有正在闯入禁区之感。“作为知识的理论,‘科学的科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社会学的特征;而作为社会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的特征”。((K.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4页。))不应该把知识社会学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学认识论,而应该实实在在地属于社会学领域。虽然兹纳涅茨基没有专门论及这一点,但人们可以猜测他已经发现了他的先驱在这方面的严重缺陷,也许少许例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曼海姆的普遍相对主义或关系主义,明显在把自己引入困境。正如古代克利特岛人,他们声称所有克利特岛人都是撒谎者,这实际上否定了他们自己之陈述的真理价值。曼海姆的情况同样如此,他主张所有的思想都由存在决定,那么,这一主张也要应用到曼海姆本人的思想上去。人们一再同他争辩,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一概念本身缺乏有效性。曼海姆至少在其部分著作中,试图在经验性社会现象的世界之外采纳阿基米德的观点,以便能对“所有思想都由社会决定”发表论断。曼海姆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困难,并想方设法克服之(没有完全成功)。在某些后期著作中,曼海姆不再坚持认为存在的命题导致无效判断,而只是强调给定的视角可能导致片面的观点,从而避免了早期立场中的困难。他还更进一步抛弃了早期在理念王国整体决定问题上提出的多余主张。他较为谦逊地说,“在社会科学中,与其他地方一样,判断真理与谬误的终极标准,可以在对客体的研究中找到,而知识社会学无法替代”,“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K.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6),第4页。))尽管如此,曼海姆的大量著作仍然有一些段落犯了发生学上的错误,也就是说使观念的有效性或无效性依赖于社会地位。这种情况有助于曼海姆后期的学生(兹纳涅茨基是其中之一)把他的工作中可加以经验证实的部分与相当不幸地侵入认识论领域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 曼海姆存在的问题,更有理由在杜尔凯姆和舍勒身上存在。舍勒关于永恒本质的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谈不上科学有效性,因而在真正的知识社会学中没有什么地位。杜尔凯姆试图推翻康德的主张,照样会把含糊不清的形而上学氛围传递给真正的知识社会学方面富有成果的开创性研究。而特别想从社会组织的特征中导出象征思想的范畴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必须把象征思考的能力当作所有人类存在物的根本潜能,象征思想使人类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兹纳涅茨基决心为自己强加一个严格的自我否定规范:他准备避开一切涉及认识论问题的引诱。他希望进行严格科学的、实实在在的探究。为了与他的早期方法论相一致,他只是假定,每一位思想家都主张自己的知识系统是真的和客观上有效的。他相信,研究或否定这些主张的真理性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事。“社会学家必须遵守那些个体或群体为他们所共享的知识所制定的有效性标准”。((K.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5页。))不是研究者的“情境定义”而是主体的“情境定义”赋予研究以活力。无论知识系统被判定为真或假、有效或无效,都与社会学家无关,社会学家只须满足于追溯知识的起源与后果、知识的功能或功能失常。兹纳涅茨基雄辩地总结为:“当社会学家研究他们的社会生活时,他必须同意,对于他们公认为有效的知识,他们才是他唯一必须考虑的权威。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没有权利用自己的权威去反对他们的权威:他受绝对朴素这一方法论规则的约束。当他涉及他们接受并运用的知识系统时,他必须放弃自己的理论有效性标准”。((同上,第6页。)) 兹纳涅茨基不仅拒斥所有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假定,而且还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于沃纳·斯塔克(Werner Stark)所谓的微观知识社会学(themicrosociology of knowledge)((W.斯塔克:《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8)。))。也就是说,他不去亲自关心“社会总体知识气氛”或“社会系统的总体历史运动”。((同上,第30页。))他更为谦逊地把自己限制在研究知识的创造者与承载者这些社会角色及其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中。 兹纳涅茨基为自己规定了两个相关的任务:建立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专门社会角色的类型学;研究支配知识人之行为的规范模式。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调查的中心工具是“社会圈子”(socialcircle)概念,所谓“社会圈子”指的就是思想家对其发表自己的思想的一批听众或公众。兹纳涅茨基指出,至少在异质社会(heterogeneous societies)中,思想家不可能对整个社会发表言论,而是倾向于只对经过选择的部分公众发表言论。特定的社会圈子给予社会认可,提供物质或精神收益,并帮助已将听众的规范性期待内化在心中的思想家形成自我形象。社会圈子要求思想家不辜负圈子的期望;反过来,社会圈子将授予思想家一定的权利和免疫性。知识人预见公众的要求,倾向于从这些现实的怀有期望的公众角度去划定材料与问题。于是,可以依据公众,以及依据社会关系网络所期待的绩效,对思想家进行分类。 本书的重点在于兹纳涅茨基对知识人可能扮演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所作的分类。在这些角色中,他区分为技术顾问(TechnologicalAdvisors);圣哲(Sages),即那些为群体之集体目标提供意识形态评判的人;神圣学者与世俗学者(Sacred and Secular Scholars),顺次又可分为各种类型,从“真理发现者”(Discoverersof Truth)到“知识传播者”(Disseminators of Knowledge),从“组织者”(Systematizers)、贡献者(Contributors)到“真理战士”(Fightersfor Truth);他还研究了“知识创造者”(Creators of Knowledge),顺次又可分为事实发现者(FactFinders)或问题发现者(Discoverersof Problems)。 这决不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分类演练。兹纳涅茨基指出,社会圈子对知识人的要求,随着期望于他所扮演之角色的不同而变化。因此,社会圈子不会期望技术领导者去寻求新的事实,这些新事实可能会使先前已程序化的活动之正确性所持有的信念产生动摇。体制期待技术领导者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新事物。相比之下,知识创造者会由于他发现了新事实而获奖赏。知识人所扮演的每一种特殊社会角色都带有某种期望;每一个社会圈子奖惩特定类型的知识绩效。 兹纳涅茨基这本书为研究对新奇观念的接受与拒斥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本书出版后不久,默顿就在一篇评论中肯定了这一点。它使我们能确定“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于采取某种态度对待经验材料施加压力的方式”。((《美国社会学评论》,第6期(1941),第111—115页。转载于科塞和罗森伯格的《社会学理论》,第351—355页。这里引文取自第353页。))比如圣哲,现存秩序的变革者或辩护士,他知道了答案,因而就不可能去寻求可能动摇现存秩序的新事实。另一方面,学者“对真正的新事实有肯定或否定两种态度,这取决于学派系统体制化的程度:在最初阶段新事实至少是可接受的,一旦系统完善起来,学派的知识承诺就阻止对新奇的发现采取积极肯定态度”。((同上,第353—354页。))因此,通过把注意力集中于恐新病(neophobia)的结构性来源,兹纳涅茨基允许我们较大地偏离那样一种全盘主张,即主张所有组织和社会结构都必定是保守的,都不愿承认创新。附带提一下,如果兹纳涅茨基在今天写成此书(在过去可能受到了注意),他会发现这对于研究嗜新病(neophilia,即片面强调新颖)的互补结构条件同样也是有益的。在某些没有归属的知识分子中,追求新奇是一个显著特征,因为他们的公众要求他们不停寻求新的刺激物,以复兴已经疲惫不堪的智力或美学上的嗜好。 兹纳涅茨基不满足于仅仅描述知识人的各种社会角色,他还为理解这些角色的转化和取代过程提供重要的线索。例如,他指出,某些宗教思想学派,只有当他们成功地将其成员与竞争对手学派隔离开来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自己的任务。当一个神学学派失去垄断地位而被迫与其他学派竞争时,它不再依靠未经检验的信仰而是必须发展出合理的劝说模式。相互冲突的信仰系统发出的挑战,对于神学知识主要部分的逐步世俗化过程作出了贡献,原先由神学学者所占据的领域,逐渐地为世俗学者所接替。怀特海(AlfredNorth Whitehead)曾经指出,观念冲突不是灾难,而是一个机会。兹纳涅茨基会欣然同意这一点。尤其是观念的冲突为以知识探索者的开放宇宙取代圣哲之封闭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机会。 这几个例子说明,兹纳涅茨基把他的方法创造性地使用于知识生活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life)之中,这足以使本书的读者思考一些特殊的问题,并值得按兹纳涅茨基的概念框架加以研究。这的确是对他的最高奖励;他为未来之完满的知识人社会学(the sociologyof the man of knowledge)提供了一个贮藏有建设性的分析途径与概念的仓库。((利用兹纳涅茨基某些范畴的尝试,见L.A.科塞:《理念的人:社会学家的观点》(Menof Ideas:A Sociologists View, New York: Free Press, 1965)。))兹纳涅茨基异常谦虚,他不像他的许多前辈,他并没有准备提供全部答案。他的书是具有开放目标的学术著作,而他本人的角色就是一位知识探索者而不是一位圣哲。他期待着未来的读者成为他的探索伙伴而不是他的门徒。 -
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
自由市场大幅度地改进了世界各地民众的生活境遇,然而,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鄙视、厌恶甚至憎恨自由市场。为什么?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布坎南等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诊这种奇怪的心理症状。 -
知识分子的鸦片
《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 《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是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 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单,而且更空虚。——亨利•基辛格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20世纪最有开创性的书之一,是对研究知识分子的“虚妄”这一主题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本书出了要让知识分子们回归平凡务实的正道,也希望能让他们免于在智识方面的混乱不清,正是这种混乱不清造成了许多智识上的“怪胎”。——罗杰•金巴尔" -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
《权力中的知识分子》对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几位理论家——尼采、福柯、萨义德、奥尔巴赫等进行了批评性的解读,梳理他们在批评性人文主义话语系统中的地位和建构作用,阐发了知识分子与权力、体制、话语等的复杂关系。本书力图编写一篇分析报告,一面展示严谨的人文批评所具有的巨大潜能,一面说明这些潜能的界限,藉此挽救分享民主制的理想。 本书指出,在埃里希·奥尔巴赫、马歇尔·霍奇森和爱德华·萨义德这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手中,批判性人文主义实现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目标:一、它揭示了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并且,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它让知识分子向权力说出真相;二、更重要的是,它揭示出批判性人文主义思想如何最终走到极限,从而揭示出它自身的反民主基础源于国家,而知识分子则以特殊的方式扎根于权力之中。 -
哈贝马斯精粹
哈贝马斯精粹,ISBN:9787305041761,作者:(德)哈贝马斯原著;曹卫东选译 -
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
《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包括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和《人的使命》两部重要著作。前者发表于1794年,是作者阐述自己的伦理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主要著作。文中着重阐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阐述了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统一性。《人的使命》发表于1799年夏秋之交,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二部分基本阐述他过去的哲学思想,而在第三部分,费希特则把信仰当作把握实在的官能,由此可看出他从哲学到宗教的过渡。 -
群眾運動聖經
當希望和夢想在街頭洶湧澎湃的時候 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膽大妄為──賀佛爾 要說本書是探討群眾之書,不如說它是一本探討人性之書。例如:「無私者的虛榮心是無邊無際的」「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膽大妄為」。本書於1951年出版即被譽為是社會科學領域經典之作,書中充滿冷雋機智一針見血的譬喻,風格猶如16世紀散文家蒙田。至今,其名言佳句仍不斷被引用、輯錄。在初版的短期內即行銷50萬冊以上,被譯成十餘種語言,是當時許多大學政治系必讀之書,艾森豪總統還大量買來送人(不過作者賀佛爾對此舉卻說:「這表示每個小孩都唸得懂這本書」)。 賀佛爾的一生也十分傳奇,他終身從事碼頭工人搬運工作,直至退休。7歲失明,15歲復明,父母早逝,靠自學成就學問,1964年成為加州柏克萊大學政治科學高級研究員。但他仍喜歡碼頭搬運工作,他的許多思維,都是在那個環境中獲得啟發。 賀佛爾對群眾運動的思考,大都是從生活中觀察而來,他與柏克萊那些大學生們的接觸,使他了解「今天願意創造歷史的只有那些年輕人」。1964年柏克萊校園學生爭取言論自由,學生喊出:「我們不要研究歷史,我們要創造歷史」。 賀佛爾的創見在本書中比比皆是,再舉一例證之,他說:每一個群眾運動在某一種意義下都是一場移民,追隨者會覺得他們正向一片應許之地邁進。那些在某一個群眾運動初起時會急急投入的人,往往也是樂於得到移民機會的人。 -
美国知识分子
《美国知识分子》讲述了爱默生、梭罗、卡森、弗里德曼等四十多位影响美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家,介绍了其生平、主要贡献、学术地位及重要影响,有助于了解美国社会人文思想的发展历史。 -
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经历了“五四”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会在“知识探求”与“公共关怀”两者之间权衡较量、徘徊踌躇。 他们的呐喊和抗争在此,他们的彷徨和颓败亦在此;他们的伟大和优长在此,他们的渺小和缺陷亦在此。我们神往,我们也遗憾;我们赞叹, 我们也惋惜。 -
北大新语
《北大新语》,乃“北大《世说新语》”之谓也。 本书仿照《世说新语》的体例,分为授教、气节、神采、德行、雅量、真趣等二十三节,收录多幅珍贵老照片,后附北大人物志。本书采用语录体,将百余年来北大人的精彩“话语”汇集成书,在只言片语中体现百年北大的历史人物风情,读者可在细微之处体悟北大百余年的历史传统、文化气象及精神魅力。 -
追寻储安平
大概是三四年前,我写过一篇怀念储安平的文章,寄给储安平曾经工作过的报社,过了几个月,杳无音讯,于是我给总编辑先生写了封信,问他是不能登、不想登还是别的原因。过了几天,总编辑先生把稿子退还给我,没有写一个字,这是不表态的表态,我当然懂得。后来,有一位朋友见义勇为,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同储安平有点关系的一家杂志,可是也是石沉大海…… -
良知与担当
《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系统地梳理了法国知识分子从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所走过的历程,对他们在法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变迁进行了深刻剖析。《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能够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总结本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非凡经历时提供一个参照对象,从而有助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社会角色进一步做出正确的定位,更好地发挥自己应有的独特作用。 -
知识分子立场(三卷本)
民族主义是一种不太系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它强调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传统,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保护和传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和疆界的完整。民族主义又是当代所有意识形态中最不依赖烦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传播地域广,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然而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到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接受。 民族主义不同于民族立场,一个反对民族主义的人可以同时是一个爱国者。但是这种常识即使是在学术界也有人时时忘却或从不曾注意。因此才会有民族主义论争,民族主义才会成为显学。 -
浮生手记:1886-1954
《浮生手记》两卷,即是《我的一生》和《流亡》合辑,在1953年《我的一生》自序中,骆氏说:“我写我的一生,其目的并不是写我,而是借了我,写出我所处的时代背景。”“透过他细腻的描述,将一部中国近代史以家族史的方式呈现,”从一个家庭,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遭遇来窥看中国往事。对《我的一生》和《流亡》,骆氏曾多次修改,希望后者能作为“抗战史上的一种民间文献”流布。在他的那个年代,这只能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愿望”。 -
思想與人物
林毓生教授多年來一直在思考著一個問題:「為什麼在中 國實現多元化的自由主義是那麼艱難?」本書便是由探討 此一問題為中心的各篇文章結集而成。書中,論析了自由 主義所肯定的幾項重要理念與價值以及它們之間相互的關 係,也討論了五四激烈反傳統主義的歷史成因與涵義以及 與其有關的道德保守主義的歷史困境。作者採取的觀點是 :邁出五四以光大五四,因此除了肯定五四運動所楬櫫的 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的目標外,也對五四思想的許 多實質內容與思想方式做了嚴格的批評。另外,書中重新 界定了中國人文傳統的優美質素的現代意義以及人文重建 的種種。作者明確地指出: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不 能經由打倒傳統而獲得,只能在傳統經由創造的轉化而逐 漸建立起一個新的、有生機的傳統的時候才能逐漸獲得; 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當前最重大的課題。 -
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
The influence of intellectuals is not only greater than in previous eras but also takes a very different form from that envisioned by those like Machiavelli and others who have wanted to directly influence rulers. It has not been by shaping the opinions or directing the actions of the holders of power that modern intellectuals have most influenced the course of events, but by shaping public opinion in ways that affect the actions of power holders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whether or not those power holders accept the general vision or the particular policies favored by intellectuals. Even government leaders with disdain or contempt for intellectuals have had to bend to the climate of opinion shaped by those intellectuals. 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 not only examines the track record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things they have advocated but also analyzes the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under which their views and visions have emerged. One of the most surprising aspects of this study is how often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proved not only wrong, but grossly and disastrously wrong in their prescriptions for the ills of society—and how little their views have changed in response to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disasters entailed by those views.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