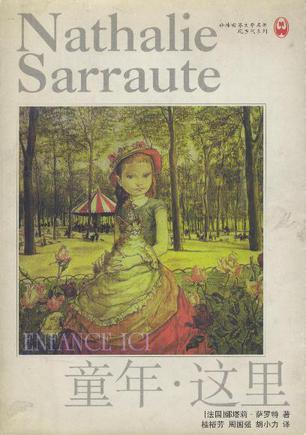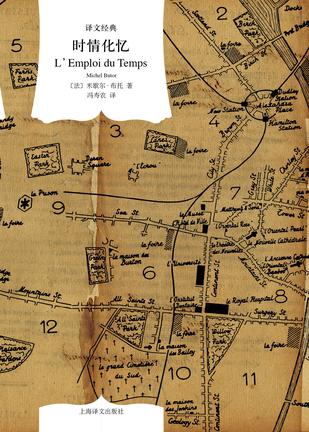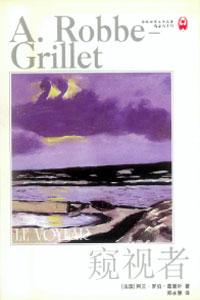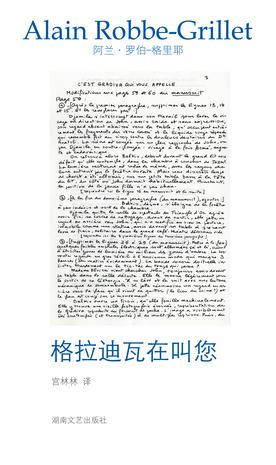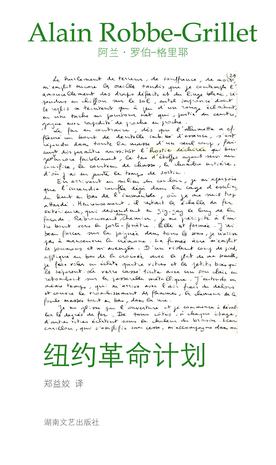欢迎来到相识电子书!
标签:新小说
-
她以前的姓 我的大公寓
《她以前的姓》:当她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在一辆公共汽车里:正在他下车之前,他的冷峻的目光穿透了她;还有几秒钟,他们之间隔着玻璃。接着什么都没有了。 二十年后,他们偶然重逢的情形并没有使相互之间靠近,他们可能会一直这样下去,如果这一点只是取决于她的话。她在这段时间里已成了名流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母亲;然而他,现在,他想要某些东西。 《我的大公寓》:我找不到我的钥匙了。而且安娜也没有回来。我因此睡在旅馆里。我的电话录音里也没有留言,除了马尔日的,她约我在游泳池见面。就是在那,我遇见了弗洛尔。她怀孕了。这正好:我也一样。 -
女巫师
自从在中学的凳子上写成了她的第一部小说,玛丽・恩迪耶就一直在营造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她的书,无论我们怎样抖动,都不会掉下什么东西来,因为书里的内容全是必不可少的.她采用一些简单的标记,没有回答的问句,各种各样的惊叹,使用我们在一个不安的、疑惑的世界里东摇西晃。她不愿意只是玩弄一些普通情感的游戏。她把那些显得过于温柔的怜悯的倾向打碎了。她弄乱了线索。她用泪代替笑。和所有伟大的作家一样,玛丽・恩迪耶让我们着迷。 在写作两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家庭故事――《在家里》和《女巫师》――之间,她突发奇想地用一种荒诞笔法戏弄了巴黎人的优越感,当然,就像加伊一样,这只是贴附在外面的一个皮层。恩迪耶更感兴趣的是将故事推向残酷的边缘:让教授埃尔曼永远回不了巴黎,让一家人永远不能团聚,这种痛苦将随着小镇的禁忌日趋合理化而成为一种快乐。多年后,埃尔曼教授准能发现,他的生命之所以被凝固是因为他完全认识了自己――就像恩迪耶认为不应当赶走尾随而至的无名动物,而应当停下脚步呼唤它一样。 -
童年·这里
《童年》发表于1983年。 《这里》发表于1995年,是她对自己创作活动,特别是词语使用的小结。 -
一个陌生人的画像
新小说反小说现当代系列 书中父女关系实际代表人类关系的普遍性:彼此需要又彼此逃避. 序 让.保尔·萨特 我们这个文学时代最不同寻常的特点之一,便是到处涌现出充满活力、非常消极、可以称之为反小说的作品。我会把纳波科夫、伊夫林·沃的作品,以及在某种意义上,《伪币制造者》列入这一类。这并不涉及按罗歇·凯卢瓦所著《小说的盛世》的方式撰写的反浪漫体裁的随笔,比较起来,我会把那类作品与卢梭的《关于戏剧致达朗贝的一封信》相类比。这类反小说保留着小说的表象和外形;这是些虚构作品,给我们描绘一些假想人物并给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然而,这却是为了让人更失望。因为问题在于这是以小说本身来质疑小说,这是在我们眼皮底下、在好像正构筑小说的时候摧毁小说,这是在写一部不该这么写、也不能这么写的小说,这是在创作一部虚构作品,它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梅雷迪斯的那些长篇巨作来说,就像米罗的那幅《谋杀绘画》之于伦勃朗和鲁本斯的绘画一样。这些怪异的、很难归类的作品并不表明浪漫体裁的衰落,而只是显示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反思的年代,一个小说正对自身进行思考的年代。娜塔莉·萨罗特的书就是这样的作品:一部可以当做侦探小说来读的反小说。况且,这就是对“侦探”小说的滑稽模仿,她在小说中插入了一个狂热的业余侦探,此人迷上了一对平庸的男女——年老的父亲和已不很年轻的女儿,他窥视他们,跟踪他们,有时远远地透过一种思维的传导猜测他们,但从来弄不太清他寻找什么,而他们又是什么。何况,他什么或几乎什么都不会找到。他会放弃他的调查,因为其自身的演变,好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那个侦探,在就要发现罪犯的时候,突然摇身一变自己成了罪犯。 这是小说家的不真诚,这种让娜塔莉·萨罗特也感到厌恶的不真诚是必要的。小说家是与他的人物“在一起”,还是躲在他们“后面”,抑或藏在小说之外呢?而当他在他们身后,他是想让我们相信他留在了小说里还是小说外?通过虚构这个灵魂的侦探,这个被挡在“外面”,撞到这些“硕大无比的屎壳螂”的甲壳上,默默无闻地紧逼着那“里面”却从来也碰不到它的侦探,娜塔莉·萨罗特力求保住她这个讲故事人的真诚。她既不想从里面也不想从外面抓住她的人物,因为我们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完完全全既在里面又在外面。外在世界是中立地带,我们想呈现给他人、而他人又鼓励我们呈现给自己的,是我们的内在世界。那个世界是陈词滥调统治的世界。因为这个漂亮的词有好几种意思:它无疑是指那些最老调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已成为共同的聚合点。人人都在这里聚合,在这里重新找到他人。陈词滥调是属于所有人的,也属于我;它存于我身又属于任何人,它是所有人在我身上的存在。这实际上就是普遍性;为了把它据为己有,必须有所行动,通过这个行动,脱去我的特殊性,贴近普遍,成为大多数;并非类似于所有人,而是确切地说,体现所有人。通过这个完美的社会契入,我在一般概念的模糊之中,认同于所有其他人。娜塔莉·萨罗特好像区分出普遍性的三个向心层次:性格、道德的陈词滥调和艺术,确切一点,是小说的艺术。如果我来做那个性格粗暴的好心人,就像《一个陌生人的画像》中的老父亲,我就局限于第一层次;当一个父亲拒绝给他女儿钱的时候,如果我表明态度:“看到这种事怎么能叫人不难受……真想不到他就她这么一个亲人……啊!反正他死也带不走,别怕。”我就投向了第二层次;如果我说一个姑娘是一个塔纳格拉塑像,说一个风景是一幅柯罗的画,说一个家族故事是巴尔扎克式的,我就到了第三层次。与此同时,那些平等地进入这些领域的其他人,赞成我,理解我;在考虑我的态度、我的观点、我之比较的同时,他们传递给它一种神圣的特性。我已躲进这个中立的、公共的地带,这让他人放心,也让我自己放心,这个地带既不完全是客体——因为我最终是下决心呆在里面的,也不完全是主体,因为人人都能在此聚合并损害到我,不过可以同时称之为客体的主观性和主体的客观性。既然我宣称我不过如此,既然我抗议说我没有隐秘,我便可以对此发议论、激动、生气、表现出“一种个性”,甚至作一个“怪人”,也就是说,以从未有过的方式将陈词滥调汇集起来,因为事实上就是有一些“普遍的反常现象”。总之,人们允许我自己决定在客体的范围内保持主观性。我越是在这狭小的边界内保持主观性,人们越是感谢我,因为我由此证明主体没有任何价值,不必害怕它。 娜塔莉·萨罗特在她的第一部作品《反应》中,已经在展示女人们是怎样在陈词滥调中沟通一致的:“她们说:‘他们之间闹得不可开交,无缘无故就吵。我应该说在这一切中我同情的还是他。多少?至少有两百万。不算别的,只是约瑟芬婶婶的遗产……不……您想怎么样?他不会娶她的。他需要的是一个会持家的女人,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才不呢,我告诉您,错不了。他需要一个会持家的女人……会持家……会持家……’人家从来都是这么对她们说的。感情、爱情、生活,这是属于她们的,是她们的领域。她们一直听人家这样说,她们知道。” 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言说”,就是所谓“人家说的”,说到底,就是不真实。有不少作者大概附带地触及过、划过不真实的那堵墙,但我从没见过有人故意以这个主题写一本书,因为不真实是不浪漫的。相反,小说家竭力让我们相信世界是由一些不可替代的个体组成的,他们全都美妙、激情、独特,甚至包括坏人。娜塔莉·萨罗特让我们看见了不真实的那堵墙;她让我们随处都能看见它。而在那堵墙后面有什么呢?恰恰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或几乎如此。只有一些茫然的努力,想逃避那暗中猜测出的什么事情。真实性,与他人、与自己、与死亡的真正关系,到处都被提及,但却隐而不见。人们在逼迫它,因为人们要逃避它。如果我们看一看人的内在世界,就像作者邀请我们去做的那样,我们隐约可以看到那纠结在一起的、软弱无力、如触手般向四面伸展的逃窜。有逃到物品中去的,它们平静地反应着普遍和永久;有逃到日常工作中的;有逃到平庸琐事中的。书中给我们描绘“老头”为了核实女儿是否偷了他的肥皂,赤着脚穿着衬衫扑向厨房,这才勉强躲过对死亡的焦虑,我几乎没读过哪个片断比那一段更使人印象深刻。娜塔莉·萨罗特看到了我们内心世界最本质的东西:搬掉陈词滥调这块石头,你就会发现一些溶流、涎沫、黏液、游移不定的变形虫样的运动。她写黏糊糊、活物一般的酏剂那离心的缓慢爬行,所用的词汇之丰富,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的思绪仿佛一种黏糊糊的涎沫渗透到他身上,贴着他,暗暗地覆盖到他身上(见《反应》)。”瞧这个纯洁的小妇人“在灯下静静的,就像一株脆弱、柔软的海底植物,身上覆满了游动不定的触手(同上)。”这些摸索的、令人羞愧、不敢张扬的逃避,就是与他人关系之本身。因此这神圣的交谈——陈词滥调照例的交流,掩盖了一种“交谈之下的交谈”,那些触手便在这一层面彼此紧贴着,轻轻触及,互相吸附。首先是有一种不自在,因为如果我怀疑你不是毫无保留地、不折不扣地跟你所说的陈词滥调一样,我那些软绵绵的怪物便苏醒过来,我害怕:“她蹲坐在扶手椅的一角,伸长的脖子扭来扭去,眼睛鼓起来:‘是啊,是啊,是啊。’她说,对一句话的每一个部分她都摇晃脑袋表示同意。她柔软、扁平、光滑,只有两只眼睛凸出来,让人害怕。她有一种使人焦虑、令人不安的东西,而她的温柔咄咄逼人。他感到无论如何他必须纠正她,让她平静,但这只有某个具有超人力量的人才能办到……他害怕,他就要乱了方寸,他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要考虑一下,思考一下。他说起话来,说个不停,谁都说,什么都说,他开始坐立不安(就像蛇在音乐下?鸟在蟒蛇前?他浑然不觉),要快,要快,别停下来,一分钟也别耽搁,快,快,趁时间还来得及,要劝诱她,抑制她(同上)。”娜塔莉·萨罗特的书充满了这种恐惧:有人在说话,有件什么事就要爆发,它蓦地照亮了海蓝色的心灵深处,而人人都将感觉到心灵中那游走不定的淤泥。接下来事情却并非如此:威胁驱散了,危险避免了,人们又重新开始交流那些陈词滥调。然而,有时这些陈词滥调也会崩溃,可怕的原生质一般的赤裸出现在眼前:“他们觉得自己的外形在解体,被四面拉扯,外壳和盔甲四分五裂,他们赤身裸体,没有护身,互相纠缠着一路下滑,好像坠到了井底……而此刻他们坠落的地方,仿佛一片海底景象,所有的东西都好像在晃动,它们摇曳着,亦幻亦真,仿佛噩梦里的物品,它们浮肿胀大,有着奇特的比例……一大块软塌塌的东西压在她身上,使她不堪重负……她笨手笨脚地试图挣脱一点,她听到自己的声音,一种奇怪的过于平淡的声音……”此外,什么也没发生,因为从来就没发生什么。交谈者一致以普遍性掩盖这暂时的动摇。因此不必在娜塔莉·萨罗特的书里寻找她不愿提供的东西;对于她来说,人首先不是一种个性,也不是一个故事,甚至也不是各种习惯的交叉组合,而是一种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无止无休、软弱无力的来来往往。有时,那甲壳空了,一位“迪蒙泰先生”便突然闯入,他已熟练地摆脱掉特殊性,而只是普遍性生动而富有诱惑力的组合。于是大家都舒了口气,重又燃起了希望:这么说这是可能的!这还是可能的。死一般的寂静随着他一起进了房间。 这几点评述只是为了引导读者阅读这本优秀而难懂的书,而并不试图详尽地研究其内容。娜塔莉·萨罗特最出色的便是她那种不联贯的、摸索的、如此诚实、如此充满遗憾的文笔,它极其小心地接近目标,又由于一种羞怯或在复杂事物面前的畏缩而突然离开,最终又通过形象的神奇功效,几乎毫不介入地猛地把那浑身流涎的怪物丢给我们。这就是心理分析?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大欣赏者,娜塔莉·萨罗特也许想让我们这样相信。就我来说,我想她在让人去猜测一种难以捕捉的真实、展示这种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无休止的往返、致力于描绘荒芜而令人放心的不真实的世界的同时,创造了一种技巧,这种技巧可以不用心理分析,就在人的生存本体中,达到他的真实。 译 后 记 猛然拿起这本书的人,会有些摸不着头脑,甚至读不下去。因此让.保罗·萨特作的序,可以作为一个导读。 萨特的序是对小说的一种解释。当然你完全可以作有别于萨特的另外的解释,也完全可以不受萨特的哲学引导。这部小说就像一块从包装盒里拿出来,赤裸裸地放在盘上的蛋糕——开放的,毫不设防的,没有秩序的,你从哪个角度去切开它,送进嘴里,都可以。 我则要建议读者,对这类小说,名之新小说也好,反小说也好,要去感觉。就像坐进浴缸里去感受水温,站在风里感受速度的磨擦,走进雨里感受水的润泽,因为你需要进入的是作者极其敏感的精神世界。就像一些只有舌头特别敏感的人才能品尝的美味,它没有浓烈的味道,不能麻痹你的舌头,只有在细细的咀嚼和慢慢的吞咽中,才能口中留香。一层层剥进去,直到深入人性的最里层。与作者一起去经历人的每一种感觉。在这里,物质的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的世界)被淡去,我们进入了一个感官的世界。人在自己的感觉中活着,他不光是物质世界的奴隶,更是自身感官的奴隶。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自身观念的四壁之中活着,永远在“感觉”与“真实”这猫捉老鼠的游戏中疲于奔命。我们摆脱不了我们的感觉,就像摆脱不了呼吸一样。 记得同样被归类到新小说作家之列的阿兰·罗伯*.格里叶对新小说曾作过这样的解释:“作者已不再是要求读者接受一个预先完成的完美、充盈、自我封闭的世界,而是相反,要求他参与到创作中去,也去创造作品和那个世界,因而学会创造他自己的生活。” 我们无需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书中父女之间的关系,也无法用心理分析来探究书中的“我”这个心灵探秘者的精神状态。萨特在序言中说道:“不必在娜塔莉·萨罗特的书里寻找她不愿提供的东西;对于她来说,人首先不是一种个性,也不是一个故事,甚至也不是各种习惯的交叉组合,而是一种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无止无休、软弱无力的来来往往。” 在萨罗特的笔下,人首先被剥离开这个世界,其次又被剥离开他自身的那张皮,她像拿着手术刀的外科医生,置身度外地、无动于衷地让我们看手术台上的那个病患。他已毫无遮掩,既不可以躲在一个故事里,也不可以躲在一种关系里,面具、皮囊全都被揭去,一个浑身渗着黏液、血管奔突、淋巴腺跳动的怪物。她的笔就像一把手术刀,从不停留在静态的描写,从不停留在人和事的表面,而是探进去,极力钻透表面那堵墙,伸到平庸的普遍经验之下,抖落出人们刻意掩饰或无意识的世界,也就是戏剧表演的幕间世界。而这却是以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最平庸的描写来完成的。因此有评论者称新小说是“后现实主义”,也有一定可比性。以《一个陌生人的画像》而言,全篇可以说就是一双窥视的眼睛和窥视者内心的独白。书中父与女的关系实际代表着人类关系的普遍性:彼此需要又彼此逃避。这种象征性即使在刻意为之的松散、无秩序的文字下,也能让人觉察出来。新小说在其云山雾罩的文字之下所追求的其实就是现实,不断地穿透不真实的那堵墙,寻找的就是真实。 这种书要慢慢地读下去,读之有味的人,会越看越耐看;读之无味的人,翻不过两页;还有第三种可能,便是读之无味,弃之可惜。多数爱好者都属于后一类。 娜塔莉·萨罗特1902年生于俄国,两岁即到巴黎。学法律出身,曾作过律师。直到1939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反应》后,她才完全投入文学创作。1948年,萨特为她的第二部作品《一个陌生人的画像》作序,从而向文坛宣告了一种新型小说家的产生,以及“反小说”的诞生。萨罗特于旧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10月19日去世,享年99岁。她一生写作相当有节制。也不像其他法国女作家那样,总有一些花边新闻。新小说是否自她而始,没有定论,但提到这一流派,一般文学辞典或文学史,首先提到的便是她。新小说作为对传统小说的一种反叛,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史上的确有一定影响;可以说,它是以走到极至来触动既成事物;但也如极端的东西一样,势必只能如流星一般。打破小说写作的一般规律,破坏读者的阅读习惯,是这类小说表面上的共同特征。小说自动放弃大众,新小说不是始作俑者,但却是最极端的。的确,古典浪漫小说创作的登峰造极,及电影、电视的相继产生和发达,小说“说故事”的功能大大被削弱了。新小说的意义在于它的探索和思考,而非它之新奇。新奇是没有生命力的。新小说的创作者们大概绝无哗众取宠之意。他们只是告诉在惯性的轨道上作习惯运动的人们,还可以有另一个视角,哪怕它让你看出去并不舒服。 这本书很难译,译出是一种痛苦的经历。 但凡文字的创作,写作也好,翻译也好,人求的都是一种宣泄。但译这本书,你丝毫得不到这种宣泄,因为你走进了人的精神世界的迷宫。 边 芹 2000年3月9日 -
让·艾什诺兹
《让·艾什诺兹》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让·艾什诺兹已经在法国的文学风景里打上了自己深深的印记,这也许是因为他的作品比别人的作品向我们讲述得更好、更有力。也因为他以某种方式占有我们的时代,用他的语言和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新的文化实践和他自己的想象,用成为时代认知符号的戏拟精神和虚假的漫不经心。最后,还有在冒充微不足道的小事件上捕捉住意义的碎片的艺术。 在他的作品深处,任何相遇都是可能的:儒尔·凡尔纳和让·吕克·戈达尔,热纳·斯特劳斯和布莱希特,查理·帕克和让·帕特里克·芒谢特,小说在这变成了各种类型各个时代的各种美学实践的令人开心的博物馆,最终总是构建出某种意义。 让·克洛德·勒布伦是教授,在《人道报》上主持文学专栏,已出版过《新小说领域》。 -
工厂出口
弗朗索瓦・邦1982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工厂出口》,他选定了受到当今经济和文化体系所排挤的社会生活――罪行、失业者、边缘人、死亡、工厂、郊区、监狱――为其文学表现的范围。 弗朗索瓦・邦显然像是一个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性之后专事于底层考察的社会调研员。他本人生活在工厂的经历使他写出了最直接来自机床、打卡机、底托牵引车和嗓音的宣叙调,他的笔端常常涉及罪行、失业者、边缘人、死亡、工厂、郊区、监狱。人们阅读这些书,同时也改变着习惯上对于一部小说的期待。在邦的小说里,叙事被行动、独白和物品的清单分担着,极少有眩目的过渡和润饰。作为底层大众的代表,他的物理的、语法的方式正好是为他的作家同伴们所弃绝的。他好像是不懂得属于文学世界的语句与属于底层社会的语句有着根本的差异,他强行推动着他那沉闷、枯燥的语言机器,成为了这一代人中不合群的典型。 -
天象馆
本书展示了主人公吉赛尔少女时代的梦幻,婚后生活的不快,揭示了温情纱幕掩盖下的自私、贪婪、冷酷和粗野。 -
时情化忆
本书巧妙利用时间的分解与组合,以日记体形式,通过对一桩疑案的追踪、一段爱情的回顾,记录了主人公——法国青年雅克对英国一座迷宫般城市的探索、反抗与追忆。作品段落布局匠心独运,极富形式感与象征性;作品呈现的跌宕悬念、异国情调、宗教隐喻等,又使其不同于人们普遍认为的那种“无情节、无主要人物”的新小说派小说。该作曾获得法国费内翁文学奖(1957)。 -
望远镜
望远镜:新小说新一代作家作品选,ISBN:9787540424206,作者:(法)帕德里克·德维尔(Patrick Deville)等著;李建新等译 -
史前史
《史前史》 接着他发明了文字。从那时起就不可能后退了:人类进入了历史。不过以为对他来说一切都从这个早晨才开始,那也是错误的。人类早就在地球上活动了。在谋生的能力方面,他不如相邻的动物,野牛、野马、猛犸。他们平静的自信和实用的感官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把它们画成了岩洞壁画的主角――这些永恒的巨型画像已经有两三千年了,所以把它们与现在尚未干爆就已过时的油画相比,人们不禁会感到好笑。 帕勒岩洞就是这样开向一大片装饰丰富的长廊。人们进洞游览。开始接纳游人的时候,这段历史的叙述者正好被任命为一向空缺的遗址导游和看守。可是他迟迟没有上任,有些事情使他脱不开身。 《警报》 芒达克只有一天时间去向参观集中营的历史学家们揭示火药对了望台的作用力,他的发现的科学的有效性就这样产生了。 由于他预感到他的女儿因神秘的卡尔而有危险,他同时寻思他是否以够指望他的妻子,后者此时正答应他前去赴他们当晚的约会。 许多疑问令他一直处于警惕之中。他应该离开集中营与女儿汇合,还是应该给警察打电话? 《野餐》 塞那尔森林中的一个平凡之日,为了和几个旧友一道野餐,路易毫无兴致地带着五岁的女儿波丽娜一道赴约。他没有看到他的朋友们,因此他就去找他们。他迷了路,而且,他还不见了他女儿。他去寻找,但找不到。相反,他见到一个女人,漂亮而迷人的女人。但是,当一个男人的女儿刚刚不见了时,再漂亮的女人又能让他做些什么呢? 《清算》 对阿尔图尔・克莱恩而言,这个夏天开始得还算好:他在西班牙中部驾驶一辆敞蓬赛车,佩蕾洛普一只手伸到他衬衫底下,而且,在汽车后座上,一只手提箱里塞满了银行钞票――是啊,这个夏天开头不坏。 只是这笔钱是他们刚刚从塞扎尔那里偷来的,而且佩蕾洛普嫁给的也是塞扎尔――克莱恩的老板。和所有的老板一样,塞扎尔不是那种喜欢分享的人,他肯定想把属于他的――女人和钱――收回。因此,对克莱恩而言,这个夏天也许开始得好,但还无任何迹象表明这会持续下去。 更何况,现在他停下车加油,他本应想到永远也不要把一个女人留在一辆装有许多现金的车上。显然,在与他有关的事中,这个夏天的结果有可能会比开始时要差得多。 尽管还有索朗日。 -
窥视者
《窥视者》是格利耶1955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叙述的是一桩奸污谋杀幼女案。主人公马弟雅思去他童年生活过的海岛推销手表,上岛后他租一辆自行车去了一位水手的姐姐勒杜克太太家。他看到镜框里有一张照片很像自己少年时的女友维奥莱,那是这家13岁的小女雅克莲。但一家人都恶毒地咒骂小女孩为坏孩子。马弟雅思的手表没卖完,想回去却误了船点。他打算租房子住下来,却发现口袋里有早晨捡的绳子,并少了3支烟。第二天渔民发现失踪的雅克莲的尸体躺在海草上,其女友推断为谋杀。马弟雅思去旧相识马力克家,听到一家人吵闹,认定儿子于连是杀人凶手,于连一声不吭只注视马弟雅思。马弟雅思又去案发地,于连在岩石后窥视,看见马弟雅思扔掉一件红毛衣及糖果纸,他虽目睹一切却没有告发。马弟雅思在推销了两天手表后回大陆去了。 -
格拉迪瓦在叫您
马拉喀什,古伊斯兰教徒区由小路和死胡同所组成的莫测的迷宫中,一个东方学家疯狂爱上了一个年轻而美丽的女奴的幽灵,传说从前她在非常情境中被杀害…… ——阿兰·罗伯-格里耶 -
纽约革命计划
《纽约革命计划》是一部结构复杂、元素繁多的游戏式的作品,它显然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包括各种通俗文化。汤姆·毕晓普说:“这就是纽约的淫乱与犯罪的神话。它向我们指出,美国的大都市好像就是凶杀、强奸和色情狂的联欢节。”而罗伯-格里耶则说:“我可以说出一座真实城市的名字,同时描写一座完全想象出来的城市。” -
昂热丽克或迷醉
法语版的原书简介: Ce second volume des Romanesques de Robbe-Grillet fait, dans une certaine mesure, suite au Miroir qui revient. L'auteur y poursuit, en effet, sa recherche aventureuse à travers les souvenirs de son enfance et de son adolescence qui ont laissé des traces, transformées, imbriquées, récurrentes, dans l'œuvre de l'écrivain ou du cinéaste. Mais, cette fois, ce sont surtout les imaginations érotiques du petit garçon qui occupent le devant de la scène, en même temps que les réflexions de l'adulte sur le rôle joué par le sadisme et le crime sexuel dans la fantasmatique masculine. Cependant, la “ jolie fille ” y apparaît bientôt comme le contraire même d'une simple victime, brillant soudain de tout l'éclat d'un piège éblouissant : le charme mortel de la sorcière. Ainsi la Grande Guerre quitte son visage de boue pour se dérouler à présent dans une sorte de forêt enchantée, où dragons français et uhlans prussiens sont aux prises avec des fées-fleurs aux troublants sortilèges, dont on est en droit de se demander si elles ne sont pas tout autre chose que des jeunes espionnes suscitées par l'ennemi. -
逃亡者
“我应该,但却没有心境,没有品味也没有开赋来写小说。” 1943年出生,已经在午夜出版社发表了九部小说的克里斯蒂安・加伊如是说。以自谦的方式向小说发问,这是加伊写作技巧的另一种体现。 作为一名同样具有极少主义特征的小说家,加伊的每一部作品都涉及到一个空间──真理的空间、矛盾的空间,其中欲望与柔情、轻浮并存。为了获得治愈某些伤痛的喜悦,加伊习惯于揭开另一些伤疤,这就是他的那些故事既朴实无华又令人焦虑的原因。他讲述事物的空虚时,所用的却是有力的、带电的语言。这种充满断裂、缩写词和句子成分被颠倒的极富个人特色的语言,越过了沉默和谨慎的界线,声速地将空洞填满,并且赋予了事物以身体。 我们还可以说,加伊是一位爱情作家,一位夫妻作家和写夫妻生活历险的作家。他笔下的爱情故事既是艰深莫测的,又是无比精致的,一切看似矛盾的欲望和习惯集中在同一个人物身上。这一切都非同寻常。 -
吉娜・嫉妒
罗伯―格里耶在创作实践中对其作品的结构与形式的注重远远超过了作品内容的本身,本书译介的《吉娜》和《嫉妒》也反映了这一特征。这两部作品反传统小说艺术手法虽然新奇,却同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去甚远,尤其对把阅读小说仅仅作为看故事消遣的读者来说更是如此。然而,作为小说艺术的一种探索,罗伯―格里耶及其他新小说作家的作品毕竟丰富了现、当代小说的表现手法,其彻底反传统的美学思想在西方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热门标签
下载排行榜
- 1 梦的解析:最佳译本
- 2 李鸿章全传
- 3 淡定的智慧
- 4 心理操控术
- 5 哈佛口才课
- 6 俗世奇人
- 7 日瓦戈医生
- 8 笑死你的逻辑学
- 9 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
- 10 1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